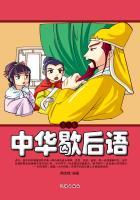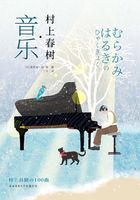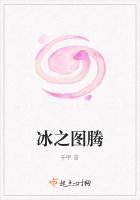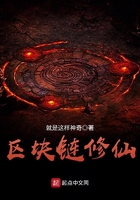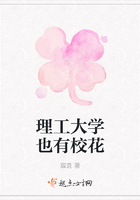风中的文竹
秋日,植物的绿不似夏天那么喷薄而出,她不再想着生长,呈四处蔓延之势,而是将生机往内里一点点敛藏。
秋天的燥火反映在我的口腔溃疡上,反映在儿子脸上又多出的青春痘上。似乎对植物也不利。文竹——我家的一盆绿色宠物,一周来家里没人光顾,也得了与口腔溃疡和青春痘相似的病症——遭遇了干旱的谋杀。
向上攀援的幼嫩芽尖,忽然枯黄了,犹如青春被掐断生命之流,突遇危涯。不仅嫩须无法继续前行,茎也彻底殒身,香消气断,垂首枯萎。看形状,毫无回春的神气儿。
想她焦渴至极,无法支撑到主人回家的时日,她那刚刚萌生的努力向世界伸延的舌尖,无法舔到滴水甘露。想起她在燥热的秋老虎天气里蒸腾出的那份烧灼,那份望眼欲穿,内疚、惋惜啃噬着此刻的宁静。
不久前,英国《每日邮报》刊出一幅照片,一头北极熊正在海浪中挣扎。因为全球升温冰面渐远,北极熊眼下要登上距它最近的冰面,竟需游过大约六百四十四公里。它们可能因超负荷游泳力竭身亡。同样的道理,我家的文竹也是因为游不到下一个时间之岸,才出现了“过劳死”。
于是,我回到家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用为她事先准备的水给她浇个够。为了养好她,平时我预备了两个大的饮料瓶,一个用来装白水,放在窗台上晒,这种经日光晒过的熟水性能温和,适合浇花。另一个是自制花肥,堪称文竹的大餐,这是我的发明。因为花卉市场搬得更远了,买花肥不方便,于是我想出一个笨方法,将吃剩的猪的、鸡的、鱼的碎骨从瓶口塞进去,倒入水,拧紧瓶盖,任其发酵浸泡,隔两周上一次肥。
文竹有大餐吃又有水喝,长得自然精神。她的生长好像不受季节限制,虽然到了秋季,她却并不理会此时的肃杀与瑟冷。在我的及时挽救下,她获得了新生,便以加倍的速度生长。这种生长像变魔术,今天你发现根部冒出了一枝新芽,正在欢喜时,冷不丁在别处就会发现另一个。
第二天清早再看,新芽已蹿一尺许,且又有新芽冒出,互相比肩,争相直指,仿佛战争地图上攻打取胜的红箭头,不停息地指向一个又一个城垒。生长的势态是流动的、暗暗的,但又是分明的。
像是早已在根部憋足了劲,等着一展宏图。许是我自制的花肥暗中起了作用,文竹的生长简直不管不顾,不知那一盆沙土蓄谋着怎样的能量。有朝一日,她强劲的根须或许会穿透瓷花盆,真是难以预料。
为使她的攀援有所依附,我在阳台的天花板上粘上了两个小挂钩,又把自己早已派不上用场的毛线球找来,一端小心系着“绿箭头”,另一端系着天花板上的挂钩,挂钩不够,我就系到晾衣绳上。文竹的茎梢简直具有触觉和视觉的特异功能,她沿着我设计好的路线,绕着毛线造了一把构造科学和严谨的旋转天梯。没过两天,天梯就戳到天花板了,并且又在上面谋划新的路线。
绳子扯得越来越多,每一根茎都伸展出手掌大小的淡绿叶片。叶片汇聚一起,轻如薄纱浮云,细腻温婉,柔弱风流,如才情源源不断汩汩而出。恍若宋词里削肩凝眸的女子,在纸上铺排出一行行婉约清幽的诗意。这诗只有儒雅尊贵的才子来吟,万不可让不解风情的莽撞汉子窥探棒喝。
记得那年十月的一天,我还未来到阳台,就闻到一股别样的浓辛之气。扑面相遇,却发现她身上盈盈然张开了繁星般的白花,花蕾如撒上去的黄米粒,似乎等着小鸟来啄。凑上去,一缕香杀进鼻翼。像桂花,香味又比它烈。黄白的碎花,有的五瓣有的六瓣,开遍了文竹的两根枝条。看那样子,新新旧旧已开了几日了,也许在我走后的次日就开了吧,很遗憾没有在她花瓣初绽的那天相见,仿佛情人的心,总是不能适时相遇。在一方情意最浓馨最怒放之时,另一个或曾未知,或曾远旅,或尚懵懂,因为各种因缘而错位,而抱憾,再次相见,面对的却是不堪的残局。
开花给了我意外的惊喜,原本不知她有开花的一日,以为只是素装裹绿,哪知也吐芬露芳。花虽微小,花瓣的伸展曲线却雅如百合,后得知属百合科,性喜攀援。若任其生长,则不像竹,而像藤了。呵呵,我倒喜欢她藤一样自由自在地攀爬,裸露自然天性,在阳台的一方天地手舞足蹈,把这里营造得葳蕤丰茂,翠云重叠才好。虽然她名曰文竹,我却愿她野起来,也不准备像别人那样给她限定造型,心里怂恿她快快长,随意长,把一方阳台都扯起一枚枚小绿旗才合我意。
母亲来我家,我引她到阳台看我养的文竹,母亲惊喜养得这么好,并谦虚道:“家里我也养有一盆,可养不好,到底是文人。”母亲的潜台词是,文人养文竹就是不一样。
母亲把文竹的长势与女儿的文字生涯结合起来倒有趣,也许有点儿冥冥中的相通吧。文竹知我心,会我意,目光相交,心领神会,我的怜爱明明已将她揽在我目光之中。她长出一点点儿绿,我便欣喜,每次有所不同,我便有感于她的成长。因为不仅为她,在我看也为我,她的根中植满了生命的惊喜,在空气与阳光中慢慢拓延。
每次周一离家,我都要喂足她,因为有一周的时间与她相隔。秋冬之季,为防干燥,我采纳了爱人的方法。用脸盆蓄水三分之一,轻轻放在盆竹底部,让水汽慢慢向上输送,不至于等我不及。这个法儿果然奏效。每次周末回来,她都神色自若,安好无恙。
算起来,这盆养得骨骼健壮、葱茏雅丽的文竹落户我家已有几个年头了。最初它长在一个小瓦盆里,像一个婴儿被裹在蜡染的印花襁褓里,声息微弱。
那天下班,在丁字路口遇到一个卖花翁,便看上了这撑着两片绿云的小生命。想到儿子即将中考,这片怡人的绿或许能抚慰儿子的紧张情绪。这样想着,小小的交易之后,她就归属我了,落足在儿子棕黑色的写字台上。
男孩子毕竟不是莳花弄草之人,管理她的自然是我。初并无大事,后来顶端黯淡干枯,了无生气。于是掺入沙土,等于给她造一个好肺,这样花盆透气,文竹才呼吸得好。
想起母亲养花的经验,似乎提起倒盆之说。若养得不好,一定要倒盆,换一个更好的空间。
照此,换上一个大花盆,再把袋里的沙土倒入,与原先的土两掺,搅匀,再请文竹搬家。
文竹从小居室换到一个大居室,豪华气派,“床”也松松软软,自然要伸胳膊伸腿,舒舒服服地长啦。
爱人说,应该到阳台去。还别说,阳台竟成为她的乐园,在这里她迎来了生命的欢欣与绽放。
后来,我的工作换到了另一个城市,与她不能日日厮守。但她并没停止生长。我不在的日子,她独自守着自己俊秀寂寞的绿,每一个小小的叶片都在巴望我的归期,她细细嫩嫩的茎叶,像极刚出生婴儿的手指,让人闻见那新生无邪的气息。
她住在我卧室外的阳台上,站在阳台的纱窗旁,每日沐着日光,高楼凉风穿过她如今繁密的枝枝叶叶,风的小手摇晃着她绿漪的梦。由此我想,她一定最喜欢风吹了。
夏夜的风,秋夜的风,白日的风,黑夜的风,每时每刻,她呼吸着风的营养。
——她太贪“风”了。说起来,她太调皮,太野了吧。因为风是最广博的。风穿过世界的角角落落,见识过山河洋流、森林草地,与不同肤色的人群打过招呼,听过不同的语言,闻过不同地域的气味。风的心胸、味道、强弱、冷暖,乃至色彩、质地、方向,自然都是有一定来历和说法的。所以,每一缕风都是新鲜的、多识的、智慧的,风是生长者的老师,打开愚钝者的心窗。风也是迷惘者的向导,使生命长出清晰的脉络。
她正处于生长的青春期,身体的各个部位正在发育,手脚都令人惊异地生长,枝条内欢奔着生命的河流,羽状的叶片是一片片划摇的桨,又是振奋的羽翼,呈现出翩翩欲飞之态。我喜爱的,便是她有着蓬勃而秀逸的外观与精神之美。这种美,是朴素的植物美。
因为她撷取了世界的精华。她聪明地选择了自己生长的位置。沐浴着不同方向风潮的吹拂与洗礼,再加上主人给予的物质营养,才孕育出如此风韵饱满的身心。
她最喜欢纱窗旁边这个位置了。
是的,她的生长正是以阳台为起点的。因为风是从这儿进来的,尽管窗常常闭着,但风还是从缝隙中钻进来。这是她迎接风的一个关口。她会意四季风的来历,她会根据风的不同调整自己的姿态。她慰问风,点头,嬉闹,或者让风静静地上一节讲座,她能听懂风的意旨和密语。在东西南北风的吹拂下,她渐渐历练长大,渐渐明晰世态。
因为第二天,我能从她新绽的梢头看出,这丫头又长出息了。她为这世界贡献的不仅是新绿,还有新知。
文竹的脾性原来喜欢风。这是我侍养文竹的最大发现。这样,她才能长得痛快,长得放肆,即使冬日里隔着阳台上的一层薄薄玻璃窗,温度也并不成为问题。
而今,阳台的天花板上已扯满了层层绿荫。想起一句诗,“一棵树生长得超出了它自己……”我用这句诗来仰望她、表达她。
而我与文竹相伴两天后,也要离开家了。
到外面的风里去,不同方向的风里去。列车裹来的风,每一位旅客身上的风,飞鸟从远处衔来的风,河流从远处漂来的风,书页上每个字传来的风,话语背后藏匿的风……
成长深陷于色彩斑斓、无处不在的风中。
在众多的风涡里旋转,沐浴,呼吸,打开生长的细胞,轻轻地吹拂它,摇醒它,猛烈地推搡它,慢慢地,窄小的五脏六腑被充盈起来,思想越来越如风一样广袤。
在风中,列车上的我,阳台上的文竹——我家里的守候者,我们握到了彼此的手臂,听到了彼此的歌声,触到了彼此的声息。
母亲的旧话:姥爷
姥爷是那个村庄及其周围颇有名气的铁匠。我小时走姥姥家,见过那个操作台,布满了黑漆漆的铁屑。姥爷身上的侠气兴许是这种活计长期淬炼出来的。
姥爷去世时我才七岁,印象很淡薄,像黑白默片。我只记得他在自家的平房上晒红薯干,摆了满满一房顶,记不清我是怎么问的,姥爷告诉我,这些都要缴公粮的。我记得他躺在床上吸烟的样子,衔在嘴里的竹烟管足有一尺多长,这个画面一直留在我脑子里,那时恐怕他已患病卧床了。
早春时节回乡,母亲告诉我,舅想给久在地下的姥姥姥爷立碑,母亲找出一张几十年前的老照片,到相馆里用了一些技术手段,只把姥姥姥爷的头像留下来,放大成两人的“合影照”。照片上的姥爷头戴皮帽,方脸隆鼻,眉宇神情间凝聚着一股异样的绿林豪气。这让我想起他解放前当民兵队长的经历,峥嵘岁月,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所以,在我心中,姥爷似乎和一般农民不大相同。
姥爷生于1906年正月,曾外祖母给他起名正年。每到正月姥爷的生日,曾外祖母都要给他做点改样饭,最差也是从大家吃的糊涂面条里捞些稠的,让他吃好,生日快乐好多干活。
姥爷弟兄四个,他是幺儿,但也没得到特别的宠爱,十六岁时就早早去镇上学打铁。
那时当学徒是不挣钱的,师傅只嫌做的活儿少,每天天刚亮,姥爷就得起来打扫前后院,然后挑满水缸,晚上还得喂牲口。
姥爷在师傅家连张睡觉的床也没有。师傅怕他晚上困睡不醒,误了给牲口添料,只让他睡长凳,如果掉下来,正好“起床”给牲口添料。师傅的这点刻薄刁钻和发明半夜鸡叫的周扒皮竟是一个样儿。
因为当学徒不挣钱,姥爷连鞋也穿不上。姥爷担铁去几十里外的薄壁,一路上都是赤脚走,走得脚板发热。路上又要冰凉的河水,发热的脚板与冰凉的河水相激,使得姥爷老来落下脚后跟疼的病根儿。母亲每逢路过那条河,想起姥爷赤脚河的情景,眼睛就会潮湿起来。
姥爷脾气倔,但心地仁慈宽厚,及至他做了师傅,对徒弟视同己出,全无那些严苛的规矩。姥爷怜贫济苦,村子里的街坊邻居,乃至三里五村的人都愿意来姥爷家定做铁货,修理农具。那时,辉县很多农民用的镰刀上都印有“房”字。姥爷靠这个手艺支撑着养活了全家。
母亲是姥爷的四女儿,很小就学会了记流水账,通过查字典或向别人请教,学会了课本里学不到的字词,说起来有“辘轳、葫芦环(井绳上用)、毂须、套搭儿”等农具名儿。虽然记了账,也有好些人不还的。有的是没钱,有的是想沾个小光,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因为这次不还,下次便不好意思再来做活儿。
母亲说,村里有一家每年都来修锄头、镰刀等农具,整整修了两年才背来一袋麦子还账,姥爷让他把粮背走,对他说:“你家人口多,让孩子们吃吧,我这里过得去,以后不要还了。”
姥爷要母亲把账抹了,母亲想不通,既然如此,何必要记账呢?姥爷给女儿做工作:“你得分清人,他家穷得叮当响,我只当给他帮点儿忙。好歹赖账的人不多,有钱的人不拿现钱咱还不给他做呢。”经姥爷一说,母亲心里一下亮堂了,这种区别对待是有道理的——你不挣有钱人的钱,咋能救济穷人呢?
母亲姊妹几个后来都能上学受教育,得益于姥爷是匠人,除种田外有份收入。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的开明思想。村上有好些保守的人不让女孩上学,说是长大了还不是给她婆家挣钱。但我姥爷不顾这些,让子女们只管念书。
饥荒年代,姥爷领全家去山西、安徽要饭,最小的女儿被迫卖给地主人家,吃尽苦头。回乡后,姥爷又当了村里的武工队队长,扛起了枪,披着血布衫干了两年,才得以翻身解放。母亲常常讲起印象最深的一次:姥爷带领小分队到附近的五里河村参加战斗,因怕被发现,从村里出发,滚了一里多的麦地……这场战斗之后,五里河的十几口枯井填满了日本兵。
姥爷打过游击,在村里有威望。解放后,村里分地主的财物,让姥爷挑,姥爷把最好的全让给别人,别人挑罢姥姥才捡几件。村里把地主的楼房分给姥爷住,姥爷也拒绝了,让给乡亲。自己则平了一块地基,盖了三间平房,孩子们都是在自己父亲盖的房子里长大的。
姥爷坚持“饿死不吃救济粮”。别人都去村公所领救济粮,姥爷不让姥姥去。看到人家吃大麦面、豌豆面,孩子们都眼馋,姥爷对孩子们讲,人要长志气,救济粮是救懒汉的。从母亲零零碎碎的回忆里,一个铁骨铮铮、血性倔强、仗义多情的中原汉子形象被勾勒出来。
姥爷五个女儿,在舅还没出生时,他就提前为自己准备了棺木,那时他才四十多岁。棺木是一副他满意的黄楝木。为了伐这块木头,姥爷费尽心思,上树时还摔坏了腰。这副木板平时就是母亲的睡床。母亲说,这副棺木让姥爷伤透了脑筋。
村里办食堂时,国家改革殡葬政策,下葬时不准用棺材,谁家备有棺材都要归公。中国人向来重视自己的身后事,即使一介普通百姓,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也有妥帖周到的安排和考虑。姥爷当然舍不得将辛苦预备的棺木充公,晚上偷偷把它埋在猪圈旁,才躲过了风声。但老埋在地下也不是回事,姥爷担心板材会沤烂,过几天又把它偷偷挖出来。这一挖不要紧,很快走漏了风声,大队让拉到村里小学做课桌。
想必姥爷一定为此大伤了一番脑筋,后来棺木还是从学校拉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