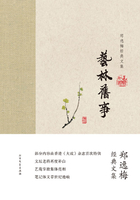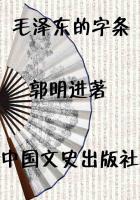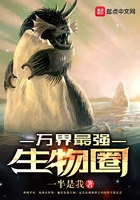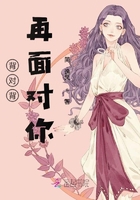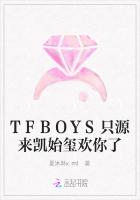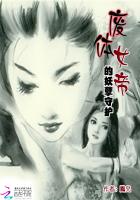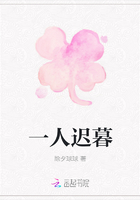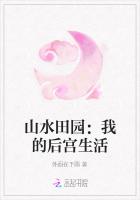接着听说报社一位夜班组版员在回家路上遭劫,不禁一惊。有一天和这个被劫女孩一起吃饭,才听到事情的经过。她家离报社不远,从没打过出租车,都是骑自行车。那天下班不到十二点,她骑着车,手包放在车篮里,左手还缠了几下手包带,一劫匪从后面瞄上她,劫匪抢包的强大冲力使她仰面倒地,胳膊、背部都有摔伤。她说,几步开外就是一个派出所,灯光从窗口透出来,正照在马路上,那劫匪还是跑了。
那几日,某市记者午夜在小区门口遇害的消息也在各媒体报道,炒得骇人听闻。想起种种可怖意外,平常的气氛中也显得惊悚。于是,回家途中像一个地下党留意着前后行人,脚下紧走,并掏出手机佯装与家人联系:“你来接我?好的,看见你了!”
终于安全钻进小巢,就像胜利抵达解放区。洗漱完毕,泡一杯菊花枸杞茶放在床头柜上,躺卧着饮上几口,算是睡觉前放松的小插曲。
此时,星月西沉,报社仍有最后一批同事在坚守,一级比一级高的新闻大员,检验、把关,一个个站在版面付印前的流水线上。事件、故事暂且在这里沉寂,等到付印那刻,等到明日晨曦初现,人们吃完早餐,散发着墨香的报纸便落在千万家市民手中。目光注视的刹那,近在眼前的卖瓜事件、城管执法,远在天边的宇航员太空飞行、领土争端,林林总总,芝麻西瓜,一起涌入眼帘,争相发言。
广告部
曾经在一个专刊待过,对广告部的生态略知一二。
如果说采编部门是报社的心脏,广告部算什么呢?当然,如今媒体的生存哪一个离得开广告?全靠广告收入为媒体造血。广告收入高的话,媒体就雄健强势,冲在行业前端。收入低的话,当然就弱不堪敌,被同行甩在后面。
这家省会城市的报纸,听说以前很是辉煌,每天做广告的人在报社外面排好长的队,想加塞儿还得找关系托熟人,可想当年门前车马喧的大好形势。
如今媒体呈诸侯分封之势,且各有渗透争雄,广告部的压力可想而知了。
广告部是一个喧哗的部门。整个大厅穿行着业务员紧张的脚步,大厅靠东装修出几米宽的“二楼”,分设着几个部门主任的办公室,最南端是广告部的首脑办公所在。
“二楼”上几个领导来来往往,似乎在酝风酿雨。他们习惯在上面朝下喊人,发布命令:
“某某某,你昨天跑成了没有?”
“某某某,你要来钱了没有?”
…………
这时,大厅里开始不安,业务员心里忐忑起来,就连没有广告任务的我心里也是揪揪扯扯的,如果上面的声音开始不安,声色俱厉,我的情绪也跟着沮丧起来,好似做错了什么。
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全都是联系业务的,似乎我的存在有点儿异类。
一个叫老刘的,做过教师,在县报做过编辑。家里已娶了儿媳,却还在这里跑广告。电话里联系广告的声音总是有些气虚:“你好,我是老刘啊——”或是“哦,开会啊,那回头再联系”。准是对方在推托。
他旁边的钱小姐则不是这样,完全是另一副神采。她跑多年广告,是单位的正式人员,老资格,所以说话、身板就硬气得多。她高个儿,很有气度的样子。自信、阳光,始终微笑着,电话里总是这样亲昵地开头:“哥哥——”这是对男性。对于另外一种性别,肯定是“姐姐——”。
如果比自己小,开口就叫“美女——”,遍地是美女,所以有人说,这个叫法只是对性别的称呼。这种开头的好处是先拉近与对方的距离,也就是先用暧昧的炮弹把对方打蒙。
但也有靠自己的诚信与客户长久保持关系的,一个姓赵的小伙总是用稳重而沉厚的声音在电话里打招呼:“某某老师,你好。”他虽然没有设法在称呼上套近乎,但他的广告业绩却是遥遥领先。
其实,他们的压力都很大,假如没有业绩,怎能在广告部混?其中一个看着文雅贤淑的房产部门的业务员,因为连续三个月没有业绩,自动请辞了。
我到这里快两年了,因为竞争激烈,已经有三分之一的面孔不见了。
主任开会往往这样训话:“你们一个月不往部门进钱,部门反过来还要给你们发工资,心里可有愧?吹着单位的空调,喝着部门的水……”
每听到这里,我心里便一凛,俯下身子反省一下自己……
至少,与以前就职的报社比,这家还是大方的,以前那家报社编辑部里,每月由编辑自己凑钱买桶装水喝。现在起码可以免费喝水,也算大方了。
红灯芯绒布鞋
从小城来到都市,就像橘过淮北为枳,究竟不是原来的生态了。
先是空气。因为车与高楼密集的原因,空气中的悬浮粒若用显微镜来观察的话,一定让人难以置信,难以呼吸。而且由于建筑密集,挤挤挨挨,就像水道堵了会影响泄洪,建筑密了风也会行走不畅。再加上夏季每家的窗后都装有空调,空气与风的温度也要增加,所以都市的风都是曲里拐弯的,带着温嘟嘟的暧昧气息。
再是马路。一次和老乡过马路,我们站在一个没设红绿灯的路中间,足足等了几分钟,才瞅个空当仓皇相携而过。老乡说,这不是过马路,这是玩命!我们原来住的城市马路气定神闲,车流不堵不疾,行人过马路也没紧张感,布衣一样安适。这里却像随时有人追着你,不管身心如何,都要按它的要求奔跑起来,奔得更快一些。
怀旧就是落伍。要想在这里生存,不能老怀旧。
要想全方位地与都市接轨,并不容易。吃无所谓,因为在自己的出租屋,做些家乡菜,很简单粗陋的饭食,比如红薯稀饭呀,糊涂面条呀,只要口腹满意,没人关心你肚子里是什么货色。都市人也不会笑话你的乡气、土气、穷气。
倒是外表最能露怯,所以都市的外来妹,她们在这里待一些时日之后,就会换掉乡间带来的样式老旧、与都市流行有明显差距的衣服,然后就是模仿城里女人,也要穿低胸内衣,也要穿高筒靴子,虽然手里捏着的钱不足以穿戴名牌,但许多批发市场的衣服都很廉价。这些样式别致、风味“都市”的衣服蛮可以满足这些人群的需求。
但刚刚从乡村走出的女人,衣服可以改变,骨子里是难以改变的。因为在乡村,穿衣戴帽方面受的教育是,长短宽窄都有传统的要求。现代衣着则重在突破,要么特长,要么特短,总要制造看点、噱头,所以进入都市的女人在精神上也需有一个改良,方可与时俱进。但这究竟不是一日之功,需城市的时风时雨慢慢熏染,使骨子里的城市意识潜移默化。
所以,穿衣不像吃那么简单,吃可以关起门来保持乡村化,穿则不能乡村形象,不能大红大绿一身乡气招摇过市,这样的形象不被都市认可。要想在都市如鱼得水,就要做一条漂亮的都市美人鱼。
再说,吃与气质无关,不是说每天吃洋餐就能培养出都市气派,穿却与气质息息相关。所以穿衣启蒙之初,破绽无时不在。
朋友说,他们在省里有一个学习班,一些县乡基层的女性干部也在那里学习,几个中年女性特爱打扮,正是秋季,适合裙装,她们身着精巧上衣,下身是时兴的各式料裙。不过,一味地追求都市化,竟忘了肚皮上的赘肉,于是鼓鼓颤颤,仪容大减。可怕的是,她们自我意识良好,和她们在一起的男士又不便提出见解。不顾实际地跟风总有些好笑,比如都市女人喜欢涂指甲油,卖菜妇女伸出手来,上面也是可怕的油彩,会让人怀疑菜品的卫生。如果手形好看,十指削葱也是可意的,偏偏又短又粗的小胖手也是十指蔻丹,效果是显著了,但却可怖。
围城里有一句著名的话: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大学时老师讲到中国电影的一个特点:一旦拍到男女恋人的戏,就拍男追女,并且是慢镜头的,追呀追呀仿佛没个尽头。老师说这是在模仿外国电影,比如俄罗斯,地广人稀,恋爱的男女尽可以在白桦林之间追逐闹腾,可咱们有咱们的国情,地少人稠,大街上哪儿跑得开呀,就是公园里也不允许那样的疯跑,不小心就撞倒了人,要注意安全问题的。老师摇着头总结道,这就是乡气的都市化。
不过,在流俗的都市里,并不是所有的乡气都是可厌的。
有次在电梯里碰到一个女孩,穿着蓝色清洁工制服,脚上却是一双拙拙的红灯芯绒布鞋,脚缩缩地立着。霎时,这拂面而来久违的纯朴乡气,让人眼前一亮,它对我的震撼,一点不亚于舞蹈家杨丽萍挎着乡下菜篮出现在超市。
那一刻我想,奢华与矫情已无真实,朴素的东西才有气场。
瞬间生活史溃散的时间
一位青年作家说,四十岁之后的时间在溃散。什么是“溃散”?灰飞烟灭,洪水滔滔,一切都在席卷当中,一切都企图仓皇而逃。瞬间,本来的阵地沉寂荒芜,毫无生命的声响,成为一堆废墟。
一天晚上,忽然想起“坠滑”这个词语,四十岁之后犹如抛物线的另一半,坠滑的速度不知不觉,趋近死亡,直至无声无息归于泥土。出生到四十岁,是生命的旺盛期,是抛物线的前半截,四十岁至终点,则是抛物线的另一半。
记得有一回,市作协通知去填表,面对表格中的“年龄”一栏,不知所措,脑海中迅速做算术。但算来算去数字都不在四十以内,十分懊恼,不想落笔,与这个数字相遇令人恐慌不已,但也不想因之矫情。女人的年龄是秘密,但相貌却无法成为秘密。四十岁的女人似乎已无话可说。四十,哦,一个失去引力的数字。
儿子与情人
看完整部《儿子与情人》已是午夜。最后的结局,是与保罗有关的人纷纷退场的描写。克莱拉,这位冷艳美人,回到她的丈夫身边。她爱保罗,而保罗并没有拥有她的想法。爱有时很难说,它如此复杂。保罗只是在这种爱中寻求安慰、释放,而没有永生结合的意愿。她看到了保罗背后的那个主宰他命运的人,所以她决绝而清醒地离开了这个男人。
第二个是母亲。书中详细描写了母亲临死的情景,让人感到压抑。儿子对母亲临死时的那种心痛,“我的小宝贝,我的小鸽子”——这本是爱人的称谓却出现在儿子的嘴里,他们之间那种默契的不正常的情感,一直捆绑着儿子自由的心灵。所以他不知道如何去爱,在真爱面前一次次退缩,他这样一个拥有青春活力的散发着魅力的男青年,却失去了爱的能力。
母爱太强大了,母亲暧昧的态度使他一次次放弃。母亲的言行像巨大的罗网、巨大的阴影,使他不能在爱的天空自由飞翔。
女诗人的信笺
再次阅读了《三诗人信笺》,心里又多了一层叹息。草莓、坟墓、爱情、激情,它们像大海重重的波涛,拍击着后人的时空。
那么高贵的女诗人,却要在物质面前一次次低下头颅。她写信给里尔克,准备两人在一个地方约会,竟然问他,有没有两人在一起时所需的足够的钱。因为她此时身无分文。可叹的人!可叹的女人!读到这里,深感意外,她怎么像普通女人那样?
普通女人有的痛她也有啊,无论精神多么贵族,却也是生活在尘埃里无力挣扎的小动物,她的问话似乎带着央求的意味,细微的蚊子一样的声音,她在写这些时一定踌躇疑惑。在那样一个崇拜的顶级诗人面前。她小心翼翼,怀着一颗随时害怕受伤的心。她渴望他的爱,但终也不能免俗地带出来这句话。
“莱纳,你有足够的供我们两人花的钱吗?”哦,这探询意味的问话,把女诗人的自尊押了上去。
我把我的一个下午交给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