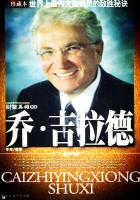顾行歌的心情……其实很不好。
本来今天晚上那个赌局,她就是打心底里觉得厌恶,有什么事不能好好的说,非得拐弯抹角,好像不是这样就说不了正事一样,而且姜正非得三言两语把她也给拽下去,好像死活要拉个垫背一样。
进门前,叶锦言好歹算是把她给放下来了,她抹黑把包放在了鞋柜上面,顺着这个事情又想到了秦思锐刚刚跟她说的那些话上面去了,一下子就变得更加烦躁,秦思锐这个人,其实是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一个人,他表面上说着了解自己是怎么想的,可是实际上却又希望自己跟他在一起后,就在他的目光所在范围之内活动,最好规规矩矩的上班下班,最好还能回来做饭。
可是对于顾行歌来说,这些都是另外一个世界之中的事情了。
她从小接受的教育,看到的东西,都是和金融有关的,顾行歌根本就不可能接受最普通的平凡人的生活。
叶锦言推门进来,看着顾行歌问:“你觉得……你还能一个人站着洗完澡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你喝了多少?”
“没多少,就是后劲儿太大,上头。也就这一次,以后见不见面都两说了。”顾行歌说道。
她说这话的时候,大概是客厅里的灯光映到了她的眼睛里,像是飞快地划过了一层冷光,非常非常的……让人窒息。
他从没有见过这么……犀利的女人。
于是叶锦言突然笑了起来,走到了顾行歌的面前。
顾行歌愣了愣,疑惑地看着他,没顾得退后。
叶锦言说:“我问件事啊……这么多年,真有男人敢喜欢你么?”
顾行歌的手指在蛋饺爪子上的肉垫上按了一下,猫咪收起来的指甲被按了出来,蛋饺莫名其妙地抬起头看着她,可笑地举着一只小爪子,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变成凶器了。
“肯定是。”叶锦言点评,“我都觉得你有点吓人,不像个姑娘。”
顾行歌低头看了一眼蛋饺的爪子,心想是挠他呢还是挠他呢还是挠他呢?语气非常平静地问了一句:“有‘姑娘行为守则’这东西么?还规定长成什么样才行?”
“那倒不是。”叶锦言想了半天,也没想出这件事该怎么形容,最后他终于搜肠刮肚出一句最不像人话的,“那什么,不是都说兄弟如手足情人如衣服么?假设说哈……情人真是衣服,那有的人是壮门面的礼服,好看,有的人是中规中矩的西装,标准,有的人是舒适款休闲装,居家,你么……”
他看了看顾行歌,给出了评价:“有点像奇装异服。”
这话音刚落,说时迟那时快,叶锦言就觉得眼前一黑,只见一大团毛茸茸地东西奔着他的脸就来了,打算给他糊上一层猫皮。
叶锦言慌忙用胳膊护住脸:“哎哟别啊,我下手没个轻重你也不担心我直接把猫给捏死?”
突然坐了一回云霄飞车的蛋饺:“喵?”
“奇装异服是吧?”顾行歌咬着后槽牙笑了笑,拿回蛋饺推开房间门准备进房间,“那也比挥着六指的爪子裸奔的强。”
叶锦言:“哎?六指的手是哪个兄弟?”
顾行歌:“我曾经的人渣哥们儿季宽!”
远方的季宽打了个打喷嚏,中枪了。
在顾行歌快要进入房间的时候,叶锦言忽然叫住了她:“哎,顾行歌。”
顾行歌:“……”
她回过头来:“有事情?”
“穿了太久军装,我现在只想穿奇装异服。”叶锦言看着她说。
顾行歌呆了片刻。
站在那里的男人看着她,眼睛里似笑非笑,却别有深意,仿佛还带着一点突然之间决定豁出去了似的笑意。
“真的。”叶锦言补充。
“我去!”顾行歌突然转身就走,撂下一句,“以下犯上,应该拖出去斩了!”
顾行歌像是掩饰什么一样,匆匆拿了衣服进了浴室,面对叶锦言,这么长的日子相处下来,说不动心那是假的,可是她又没法决定,是不是就这么相信这个男人说的话。
于是她决定扔一个硬币,让老天决定顾行歌知道自己不应该这么懦弱,可是感情不是市场,不是努力就有收获的,强扭的瓜不甜,她不希望自己好多年来第一次这么投入地付出感情,就血本无归。
那让她觉得自己就是个傻子。
正面就放弃,反面就是有希望,可以考虑答应。顾行歌对自己说。
然后他手指一弹,硬币高高地飞向屋顶……最后掉进了门和旁边的置物架的那个缝里。
面对这个操蛋的小概率结果,顾行歌呆呆地面壁了片刻,觉得刚刚做的一切都是个幻觉……
晏盛平一下飞机,就有车等着接他,他行李并不多,只拖了一个不大的小箱子,随便扔给了车里下来的一个女人手里,女人接过来,把行李放进后备箱,又掏出一本备忘录,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殷勤地回头问晏盛平:“晏总,您是先回家还是先去公司?”
晏盛平摇摇头,报了个俱乐部的名字,说:“你先把我的行李送回家,我在那边约了个朋友。”
女人眨了眨眼睛,静心修饰过得睫毛显得又长又卷,她迟疑了一下,问:“用我跟着么?”
“不用,你今天自由活动吧。”晏盛平闭上眼靠在后座上,一副不再想说话的模样,假装没看见对方脸上一闪而过的失落。
他不明原因地突然觉得有点累,可能是自己老了的缘故,对那些平时司空见惯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忽然生出几分厌倦来。
可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他的生活。
刚下飞机就去赴约,永远是一个又一个赶不完的场子,每分每秒都是钱钱钱,那些钱好像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永远也弄不清楚自己账户上的数字,只知道还不够,还要继续。
晏盛平心里突然有个念头一闪而过,他想……其实像顾行歌那样的日子也不错。
车子径直把他送到了目的地,一进门,就有侍者知道他今天要来一样,带着他往里走,走过一条曲径通幽似的小石子路,然后是花园,一边是温泉,池子中间有一个美人雕像,不知道怎么做的,有水循环上去,从她指尖眼角掉下来,落在底下的一排不知什么材料做的,仿扬琴的琴弦上,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一个小木桥架在池子上,不时有叶子从两边的植物上掉下来,飘进另外一边单独隔出来的小坛子里,力图做出些匠气十足的野趣来。
路过小池,就是雅间了,一个披着浴袍的男人等在那里,脚底下放着小木桌,一个挺养眼的姑娘在给他表演茶道。
男人两鬓已经花白,眼珠却贼亮,听见脚步声,连头也没抬,指了指对面:“坐。”
晏盛平方才车上的疲惫和麻木表情已经一点也看不见了,露出一个精神十足的笑容坐到他对面:“老张,你可越来越会享受了。”
穿着浴袍的男人抬头看了他一眼,颇有几分仙风道骨地说:“人么,年纪大了,就没那么多上进心了,总想着找个清静的地方坐一坐,喝口茶,听听水声,省得越活越市侩。有道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争来争去的,图什么呢?”
他摆摆手,总结陈词:“没意思。”
晏盛平看了他一眼,心里啼笑皆非,只觉得这话说得让他想故意捧个臭脚,都不知从何说起,只得避开他那老清新的目光,忍着鸡皮疙瘩说:“张兄是高人,境界和我们这些俗人不一样。”
谁知姓张的还没完没了了,接着说:“真正的隐士高人,乃是大隐隐于市,在市井之中悠然自得,闹中取静,心如止水。我啊,也不过就是个附庸风雅之徒,不敢当。”
这话到有点自知之明……
晏盛平认为他应该和当年的顾行歌交流交流,他忽然有点不耐烦,于是决定直抒胸臆,问:“最后一笔资金到位了么?”
老张眼珠一转,看了倒茶的小妹一眼,小妹识趣地退了出去,把门给掩上了,他这才点点头:“放心吧。”
晏盛平不能放心,毕竟这事做得不那么光明正大,于是压低了声音问:“资金来源……查得出么?”
老张讲究地用手指扣起茶杯,先闻了闻,才轻轻地抿了一口,抬起眼看了晏盛平一眼:“在国外走了两年多,进出不知道多少家银行,倒腾了不知道多少手,我都想不起来走了哪条线,你觉得谁还查得出来么?你啊!我看你真是年纪越大越不像话,越来越信不过别人,我办的事,什么时候失过手?”
晏盛平一笑,往后靠了靠,眉宇之间留下一道浅浅的皱纹,他突然转向池子的方向,看着那随风微动的涟漪,低声说:“这次回帝城,见着一个老朋友,让我想起颜清和来了。”
老张挑挑眉,等着他下文。
晏盛平轻轻叹了口气:“颜清和当年跟我说过,干我们这一行的,要么吃不好饭,要么睡不好觉,这么一想,还真******对。”
老张问:“你见着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