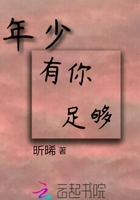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已隔世般阑珊\昨天已经去得很远\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又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日子快消失了一半\那些梦又怎能做完\你还在拼命地追赶\这条路究竟是要去哪儿\时光真疯狂\我一路执迷与匆忙\依稀悲伤\来不及遗忘\只有待风将她埋葬—朴树《且听风吟》
朱天心写,是八月,然而总有些不对。而如今,一月气聚,人儿却四处离散。哪里是对,哪里又是不对?
突然落下的夜晩。从厦门到上海的时候巳是夜里+点多。飞机晩点,从那边的白昼到这里的黑夜。地铁停运,坐大巴,从浦东到徐汇。乔木醉酒被送至医院急诊,小隆守着她。下车的时候庆幸没有雨,上海也没我想象的冷。在大马路上走的时候巳是凌晨,打不到车,我吹一口热气,拖着行李兀自走在大道上。
灯火巳隔世般阑珊。大上海在这个时候静谧得让人压抑。行人少,楼高向我逼近,只是楼层的灯光渐稀,街边路灯倒是不知疲倦地照着,照得我影子拉长,照得这块地方忽然很冷清。
昨天巳经去得很远。昨天是哪天?上一次走在这条道上是去年的寒冬,我仍是一个人这样慢悠悠地走在大马路上,从黄昏走到天色深黑才找到订好的旅馆。那时听他们讲,多年前大家一直住的是泰安,而后泰安停业整修了很久,浦江就成了下一个栖息的地方。我认得眼前的路,我喜欢这样利落的街道,让我刺目的不是街道的冷清,而是落光了叶子的法国梧桐。在南宁和厦门的冬天是看不到光秃秃的枝干的。再一次看到这些树的时候,有种莫名的遗失感,我才发现原来恍惚间一年就过去了。昨天是真的去得很远了吧。
我的窗前巳模糊一片。入住的房间号是206,狭小得甚至没有窗户。整好行李,到楼下永和豆浆点了份馄饨做晩餐,巳是接近打烊。我和黄可坐在去年坐过的那个位子。看那幅很大的贴画,我记得那时候倩雯、南楠、蒉意和黄可在这里成立了“梦”小组,回去后大家各自写下了一个同梦有关的故事。深夜里冷水汽扑到窗子前,室内放了暖气,窗子外覆上一层朦胧的水滴。我边吃边看着落地窗,却看不到外面昏暗的景致。
大风声,像没发生。上海的风同厦门一样的狂乱。大概这是海边城市特有的吧。我一直埋怨这些风吹得让人难受,即使是隔日走在巨鹿路上仍旧是大风吹着行人,总有一天会把人群都吹散。回到旅馆,在小七房里看到了小隆,他叫我,我不敢回过头应他,是有些伤感了,乔木躺在小七床上,醒了,脸很红,她抱了我一下,寒暄了几句便各自回了房。看到莫小七、贺伊曼和普鲁士蓝他们回来了,便抱着一堆吃的冲到小七房里。从厦门带了很多吃的过来。放在他床上,然后回房间睡觉,什么都没发生。第二天比赛,两个题目选一个,韩寒和寻找不是用眼睛。我选了第二个,写了小说,是一个关于铁轨,火车碾过,尸体四散和老张的故事。故事写得很温情。想到这样的场景,其实是因为近来在读吴念真的书,受了他一些影响。以前看《恋恋风尘》的时候感觉淡薄,只觉得是细微的伤感。后来读过吴念真《这些人,那些事》后,再一次看那部电影,恍觉,那些逝去的日子大概是吴念真的写照吧,真实的,那么令人伥惘。
太多的记忆,又怎么放开我的手。比完赛的那天晩上,大家去唱歌,到深夜两点多的时候,给乔木唱了那首我怎么也找不着调的《十年》后,我便走了。这首歌是去年答应了要给她唱的,那天晩上我情绪不怎么好,一下子想到去年很多人都不在了,每年这个时候总是热闹的,但热闹过后也不知道有没有再见的机会。回去后给小隆发了短信,说自己难过。我们两个像路人一样见面了连招呼也不打一个,甚至不停躲避着对方,我想起来上海前的一周,我同他说,我们还是不要见面好了。我喜欢距离感。第二天,同柳雅婷、黄可、童欣、邵晓曦走了上海一些地方。冒着小雨一路走到走到静安路303号,看了蔡元培在上海的故居,在路上看到了一些老宅,一些古旧的洋房。我说,街道砖块的颜色同掉落的红棕色叶子颜色搭起来很好看。路上凑巧又看到了上海戏剧学院,一阵欢心欣走进去,学校很小,但很有味道。走过天桥,到了金碧辉煌的静安寺。本来打算是在这里转乘车到张爱玲在常德的公寓,或者去她幼时生活的洋楼故居,但还是没能去成。最后是去福州路上的书店。在外文书店停下,去看了书,到三楼艺术类看了画册。没有找到奈良美智的画本,也没有找到弗里达卡洛的自画像。下了楼到上海书城,看书,想到去年也是一群人到这里来看书,耗费光阴,而如今,封尘不在了,倩雯、蒉意和叶璇也没有来。晩上一起窝在晓曦的房间里看恐怖片,一群文艺青年面露出大笑与惊恐。再夜些,安然睡去。
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颁奖的那天早上,黄可早早为我们到青松城占了座,我拿到了马原老师和陈村老师留下的签名。又一次拿到了一等奖的奖杯,为自己开心一阵,但更长久的是叹息。每个陌生的面孔都渐渐熟识,熟识之后要用多长的时间去慢慢遗忘。想起去年复赛时选的题目,《翻墙》,写了散文。还记得自己写的第一句话是,时光是年岁筑起的一道墙,隔着它,我们回不到往昔。写东西的人,内心总是孤独的吧,就像简娘说的那句话一样,文学,本不是为了热闹而来。每一年新概念的盛宴,会有多少人从远方奔赴而至上海,就会有多少人从这里离开。在一起共度的时光真的不长,只有短短的几天,但这几天,我们一起比赛,一起玩,一起等结果,难过也一起难过。晩上有人离开了。第二天早上也有人离开了,整个旅馆一下空了很多。
日子快消逝了一半,那些梦又怎能做完,你还在拼命地追赶,这条路究竟是要去哪儿。说到底自己不过是常常在做一些荒谬的梦。一路走来,认识的很多写东西的人转而干起了别的事,甚至很久也没有再写下些文字;有的人还在不停地写,却兀自写得忧伤。在中文系念书,长久地不知道自己的前路究竟如何,那个莽莽撞撞的年纪慢慢消沉下来,现在想得更多的是自己要怎么个活法。一直对自己说写东西是聊以自慰,看书是打发时间,旅游是为了寻找灵感,结识陌生的人是想看看不同的人生。可我越发地觉得自己孤独起来。如果说任何东西都有它的保质期,写东西也一样。那么我想一直写到腻。这世界原本该是怎么样子的?我希望它是我所念叨的模样。
时光真疯狂,我一路执迷与匆忙,依稀悲伤,来不及遗忘,只有待风将她埋葬。离开的前一天晩上,乔木递给我小隆留给我的礼物,是jasonmraz的一张CD还有几张小图和一张纸条。我又开始莫名地难受。不知道这一别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每个人总说着自己下一年会再来,可说不准到时候又有些什么事情耽搁了。上海忽然变得越发的安静,走在人群中也有种伥然若失的抽离感。我随人群浦动,似无心人偶。或许所有的相聚都是为了最终的别离。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眼前闪过的是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协大院的那几栋古旧的洋楼,蔓藤恣意攀结,缠绕得人喘不过气。浦江之星最后所剩无几的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坐着。连续下了几天的缠绵细雨,密密麻麻的叫人难受。路面很湿,让人走起路来要小心翼翼。离开的时候,也小心翼翼。
我回到降着细雨的小城,我熟悉它。上海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我从离开的那一刻就开始想念它,但更想念那群人。为文字而来,也为文字而散。
这个题目取自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伊城对帕慕克而言,是灰色的,如大雾迷蒙,他反复地呼愁,记忆这个废墟的忧郁。而我与上海的每次接触,都是降落在阴霾之中,于深夜告别。我认识她一这座城市,是从冬曰街道稀落的灯光、无叶的法国梧桐开始的。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喜欢两个城市,一个是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一个是侯孝贤和吴念真影像中的台北。前者太实,后者太虚。中学时看墨镜先生《花样年华》每每觉得穿旗袍的张曼玉一定是上海人才对,后来才知晓,原来出生在上海的是王家卫他自己。
上海的天空像罩着一张灰的幕,冬夜里无月,星光稀;而白日云浓,又仿若揭不开晴空的纱布,似镀了一层薄薄凝稠的漆,和街市高楼同染了色,化不掉,冷冰冰。
十三届的时候第一次到上海复赛,那时阿青老早就帮我们打理好了一切。房间订在华山路的那家浦江之星。十届以前,新概念的聚集地是从浦江之星门外的小巷一路往下斜穿过去的泰安,可惜那里巳不复营业。第一顿饭是边上那家东北菜馆,两大张桌子围了两圈人,当时我旁边坐的是贺伊曼和莫小七,后头是在中山读博雅院高谈阔论哲学的杨鑫,北影的钟濛也过来了,她先和莫小七深情拥抱,然后说起北京,侃各种段子。我那时是初来者,尚念高中不谙世事,看这些七、八届,九、十届前辈们在说近况聊往事,虽插不上话,但不知怎么,竟有种温暖。
复赛交完卷子那天,从上海冬天没有暖气的教室哆哆嗦嗦地出来,一路结伴往返的我看到了刚出考场的刘文。我想她如今一定不记得我是谁了,可我知道她。她是第九届的选手,在港中大读会计,要毕业了,她说这是她最后一回来新概念,看看这些老朋友。我巳经记不得她说那番话时的表情了,但我记得她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前,车子从眼前呼啸而过,尘土扬起一片模糊,声音和步伐都同时静了下来。
唱歌、聚餐、颁奖。同吃同睡同玩只五天罢了,这五天要想熟悉一个人未必太难,可这五天却结结实实地打在每一个人胸口上。走的时候大家都不舍起来。拥抱,击掌,来不及一个个告别,但都信誓旦旦说了下一年还会再来。二楼的长廊倏忽就空了,七回八转的廊路不见尽头,亦杳无音响,我锁上门,作揖告离。凌晨一二点归家,酣然睡去。
之后是什么,像各自活于平行空间一般,欲觥筹而无交错,黑白头像,鲜言寡欲,记忆逐渐模糊,直至消亡。为何旧知己最后变不成老友。
这几年,我三番五次地到上海去,春天、夏天、冬天;终究见不到雪景,枉费我每每期冀。但当我踏到这个城市的那一刻,我知道这里有我所熟悉的东西,只是刚开始觉得熟悉,便又浑身不自在起来一马路上那些跑着跳着笑着闹着一闪而过的人,哪个是和我拥有同样一段记忆的人?
你我皆路人吧。
去年七月来参加《萌芽》下半月刊笔会,饭桌上,李其纲老师给我们用黄酒兑了雪碧,他笑言苦谈,记忆真是个贱东西,五年十年后,可能你巳经忘记了当年在某个地方和哪些人聊了哪些多么高深有价值的东西,而偏偏记住了舌尖尝到过的那股极好或是极坏的味道。
那味道定是百感的才叫人如此难忘。
少年游,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
到厦岛一年有余,荒废了小说,笔也提得少了。现在是一点也想不出,高三的时候,明明巳经忙得不可开交,我又怎么会如此热血沸腾地拿起纸就胡乱涂写?那时候有太多想写的东西攒了一麻袋破烂,扎破洞隙一股脑儿就全泄了出来;现在是滴水蓄杯,总想只留着下宝贝,却难待其盈,即使想写却也不知如何下笔了。
出门即是海,身后有千山。钟声寺杳杳,鹭栖听我音。
我常慰藉自己没能在上海念书,到了闽南这地方,少了吴侬软语,坐听咿唔闽声,却也难得悠闲清静。以前马璐瑶说过想在鼓浪屿上开家书店,可现在她毕了业,一路北上,去了纪录片公司,不知是否还有这些念想。翻到手头上周宁院长为她新书(〈弘一法师传》作的序,言自己也曾想写李叔同,只是一晃便二十年,“心存夙愿,竟无所作为,终日忙于琐事,惶惶然竟老之将至”,不禁叫我感慨丛生。
在厦大念中文系的这些时日,看周围人扛着机器四处跑,在暗房里剪片,戏台上排剧,很热闹却也很冷清。这一腔的热血总归是会被时间所湮灭啊,何不慢点走,让它也走得慢些?
鹭岛鹭岛,偏居南隅。夜间孤灯,三两个好友,携半多情绪,沿白城一路行至木栈道,沙地,石砾,有风浪,亦有海声。厦门这地,月明星朗,撩人赋诗作对的情怀,只可惜缺了那点才思,只得空对月,独相思了。
也罢。这世上原本巳有足够多的诗句给我们慰藉。只是不知读诗的少年依旧否?不知年年岁岁奔赴上海的人儿依旧否?
愿少年依旧是不安的少年。
我在北京,第二年
刘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