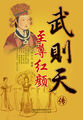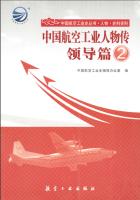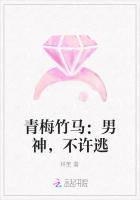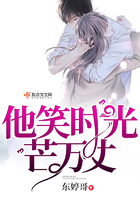周作人对此是非常明白和清醒的,他始终呼吁:"真正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文学家须是民众的领导者",好比经济政策鼓励先富起一帮人,才能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而事实却是很多知识分子大都成了国家政治变故的炮灰,被并不高明的政治把戏一再愚弄和嬉耍。他们已经把整个灵魂给了出去,而人家却仿佛把它当作一朵花似的别在胸口的衣襟上,只是作为政治手段的一种装饰品,是一种虚饰。
"民族独立"、"社会变革"、"人类解放",这些咆哮往往率先从"个人"身上踩过去。
政客们从来以国家利益至上的信条,对知识分子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是"个人"的独立、变革和解放又向谁讨要呢?自己以救世主的姿态活着,实际上却是浑身锁满了镣铐;看起来似乎每人分配了一份"自由",实际这"自由"反而是自由的限制。到最后,也没人弄得清楚"人类"、"民族"和"社会"到底是包括的哪些人。周作人实在恐惧自己所追求的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也沦为一个虚幌。
在当时的情势下,没人理解周作人的"故作呻吟"是合情理的,他的理性太不和时宜了。有作家说"人类一向有把好事搞糟的坏习惯,诸如把爱情做成贞节牌坊,把自由做成暴民四起,把革命做成古拉格群岛,使思想的龙种一次次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收获现实的跳蚤"。以此逻辑类推,周作人的理智的思虑则被骂其胆怯和无能的唾沫浇了个透透的。在新文化运动的声浪稍稍平缓下一些的时候,周作人又将自己拉回了无边的寂静。
他觉得那寂静是可亲可爱的,不过当今的人们,实在难以消受清静的恬淡,噪音虽然可怕,像污水一样漫溢得到处都是,时时地使人烦闷和暴躁,但是相比寂静,人们倒宁愿在噪音里感受自身存在的可靠性。
如今人们感到寂静时的氛围大可为两种:一种是地震时楼房将要坍塌时的那一瞬,站在房根下的所有人都不动了,抬头看这栋楼究竟那一角率先坍塌下来;另一种是灾难后的废墟上,没有一丁点儿声响的恐怖,世界上好像顿时一个活口也没有了,人只能瞪大眼睛,张大嘴,看黑夜扑扇着它乌鸦似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