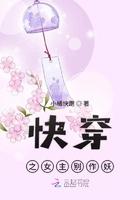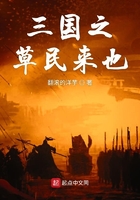当今社会的人通常对古人的人生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么人们就更应该冷静地好好想一想,以古人的才智说来,如果真可以从襁褓里蹦出个现成的"天才"、可以在黄毛小儿当中钻出一个现成的"大师",那么古人为什么会把王安石的《伤仲永》奉若经典呢?如果"天才"只是所谓的"心算神僧"或是"得奖高人",那么古人为什么没有将这类人"栽"进史册,而偏偏在陶渊明这类种田人的身上大花笔墨呢?而如果现如今的人们当过去的就过去了,又怎会再将历史书一印再印?
王国维带着只装有孤独的干粮袋,在人间寂寂地走,他是无比羡慕查拉图斯特拉的,至少查拉图斯特拉的孤独,已经被确定为伟大的、天才的孤独。
五
1906年春,辞去江苏师范学堂教职的王国维第一次来到北京,寄往住在罗振玉魏染胡同的家中,并随罗氏入学部供职。不久,王国维父亲病故,他返回家乡为父治丧。翌年三月,王国维回到北京,随罗振玉搬到了宣武门内象来街居住。在罗振玉的引荐下,王国维被派在学部总务司"行走",继而又当过学部图书馆编译,和"名词馆编修"。从此,王国维算是吃皇粮了,也同时将一只脚迈进了清王朝这口即将入土的棺材里。
1911年的中秋节,"月到东南秋正半"。即便是业已危机四伏的紫禁城,也在女儿红一般浓烈的桂花香中醉沉沉的。
之后,仅隔四天,武昌首义的枪声就打响了。外有革命党"作乱",内有袁世凯威逼,清廷解体只在眉睫。王国维与罗振玉逃亡日本京都,开始了亡命遗臣的颠沛。
王国维集清王朝的孤臣孽子与中华民族优秀的国学大师的特质于一身,没落与不朽撕扯着王国维,没落胜利了,灵魂破碎了。
"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力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唯一的重镇"(顾颉刚),学问成了他最后的藏身之所。
王国维不论是流亡海外,还是回到上海,他一直留着长长的辫子。然而,剪不剪辫子毕竟只是个形式,只是维护他作为一个传统学者的人格与尊严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