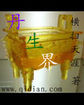就在匕首尖锐的刀锋刺破女子贴身内衣,即将划破皮肤的刹那间,岩辅突地收回匕首,插入靴中。房间里的烛光依旧静静地燃烧,甚至连烛花都没有,一如女子那平静的面庞。睡梦之中,女子嘴角浮出一丝微笑,也不知是梦到回家见了父母,还是梦到了情郎前来相救?她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刚刚从鬼门关前回来,
岩辅是个极有心计的人。
眼前这个女子,刚被揪进来时,她蓬头垢面,几乎看不清相貌。洗洗刷刷后,但凡看到她的人,都会惊异于她的美丽。也不知为什么,第一眼看到这女人,他就喜欢上了她。和猫族女孩子的性格泼辣大胆、行事风风火火、说话直言不讳相比,她显得文静,就像开在小园一角的一朵紫薇,清新、淡雅、自然,静静地散发着芳香,一经发现,会在不经意间走进灵魂深处,再也无法忘怀。而陶枝,是一束开在悬崖上的映山红,热烈、奔放、艳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享受,吸引人前去采摘。
不过喜欢归喜欢,岩辅从没轻易相信过任何一个人。虽然达托说,这女子是从山外俘获的,这只是达托的一面之辞而已。谁都知道达托早就对大巫师一职垂涎三尺,说不定她就是他派进洞中的奸细!自从发现陶枝和达托暗地里来往后,他就对陶枝产生了戒备心理。若再多个人,自己的一举一动就会暴露无遗了。
陶枝离开房间后,岩辅立时联想到女子。这个时候她会不会同样在洞中游走,查探情况呢?看到她酣睡在床时,他又怀疑她在伪装。直至匕首穿透中衣切近女子皮肤,而她仍旧毫无异样时,岩辅这才确信她的确已经进入梦乡。
回到房中,岩辅从床下拖出一只黑色的小皮箱。这只皮箱是用黑豹皮制成的,陪伴他整整四十年了。里面装着数面五颜六色的小旗,十多个没有标签的小药瓶,一卷符咒,还有几把长短不一的小刀子。此外,箱子中还有一个特大号的珐琅瓶,瓶口用一卷破布塞着,里面黑乎乎地,看不清装的啥。
岩辅从小药瓶里各倒出少许青的黑的红的粉末,放在碗中搅拌成糊糊,然后伸出舌头来,舔了个精光。
舔完后,他又搬出那个拳头大小、高约半尺的珐琅瓶,拔开瓶塞横放在桌子上。半晌,瓶内悉悉索索地爬出根红鄂黑身子的大蜈蚣,懒洋洋地趴在瓶口。
岩辅从另一个小瓶中倒出些紫红色粉末,粘些口水涂在手腕上。渐渐地,紫红色的粉末发出异香,弥漫了整间屋子。
那蜈蚣慢慢兴奋起来,向四周不断摆动触角,一对大鄂互相撞击,斗得格格作响。由于受不住异香的吸引,蜈蚣环着桌子开始爬行,探头向桌外找寻异香的来源。爬了好几圈都找不到目标,蜈蚣开始焦躁起来,越爬圈子越圆,越爬速度越快,到最后竟从后窍中喷出一股烟,腾空飞起,准确地落到了岩辅的手腕上。
彼时,紫红色的药末已然渗透到岩辅那青筋暴露的皮肤中。蜈蚣张开大鄂,径往手上的静脉血管咬了下去,嘶嘶啦啦地喝起血来。
等到蜈蚣喝足了血,岩辅脸上的痛苦表情消逝了。而他背上的青淤,也已随之变淡,几不可辨。
岩辅抓起滚圆的蜈蚣放进瓶中,重新塞紧瓶塞置入皮箱。舒展了身子,他又从皮箱中拿出那几面小旗,分插在地上布成阵势。这些小旗上绣着虎、狼、豹、狮、狐媚子、穿山甲等动物,全都张牙舞爪,作势扑人。插在最中间的,是一面由双骨交叉组成的小旗。岩辅点燃三根香攥在两手之间,盘腿坐在阵中。那面双骨小旗,恰恰就在他盘着的双腿之中、下腹之前。
岩辅对空祷告,口中念念有辞。忽然间,房中阴风乍起,扑地一下吹灭了蜡烛。黑暗之中,那三根香头上的红色火光忽地散了开来,在空中游走,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诡魅无比。片刻之后,香火倏忽间消失不见。房中再也没了声息。
这一切,让门外偷窥的陶枝看得背脊一阵阵发麻,脚心一阵阵发冷,身子软不溜丢。好容易走回房中,全身衣衫就像刚从水中捞出来,没有一处是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