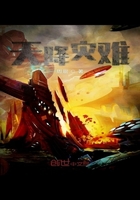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骑皆?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上元节。
及到出了街衢,程飔然才发现路征可不是带她犯禁。只因今夜是上元,整座盛京城都解了夜禁。银髓苍穹,玉盘当空。九天之下,盛京百姓们三五成群,正在太平、善和两坊中嬉游,共赏花灯。
一个小丫头挥舞着烟火折子,擦身而过,又笑又叫。少顷,又一个身量差不多的,尾随她跑过去,手中拿了一模一样的烟火折子。
“可恶。”飔然狠狠道。
路征听她叽咕,低头睇她,俊眸中有爱怜流转。“怎么了?”
她摇头。可喉头发酸,长睫忽闪,眼眶一时噙满泪水,硬是克制着自己,不许流露。
“郎君,给姑娘买杯花酒罢!”
身边有摊主叫卖。路征本无意,可见飔然哭也哭不出,摊主倒提醒了他。他取了那酒觞,递到她面前。
程飔然接了这酒,一饮而尽。酒劲很冲,她以丝帕掩口,作假着饮下。趁路征转头将酒觞还给店家时,迅速的吐掉。
待他回转身来,她颤颤的,抱住了他。
这才涕泪齐下。
“我……”
背心与腰间,都接收到了他的温暖。在清醒中做这些事,她莫名的生出一层羞涩,只得发狠叫自己不准退缩。为达目的,他想怎样都必须迎合。正叮嘱自己,下巴被他托了起来。他们那么近,那么近……他右脸一道刀尖划的红痕,清晰印刻,让她的愧疚感此起彼伏。可那明明不只是愧疚,还有心疼、难过,一起涌来。
奇怪,明明没有饮下那酒,怎么,竟也醉了。
双唇湿润一触,她全身战栗,下意识的想逃。但有他坚硬的手臂,护她安暖,也不容她避开。她很快便不支,将唇齿、舌尖一同投降给他,如胶似漆,难以分割。
他头顶那灯,有绣缂的人儿在旋转。
转的她,头晕目眩。
灯火阑珊中,她模糊的瞧见有人旁观。
那人端详他们许久,又如松鼠般翩轻溜走。
当晚她回到曳烟阁,懒懒的靠在湘妃榻上,全身松软。眯眼,阿亡正抱着有它身体一半大的精肉,狼吞虎咽。
“阿亡,为你吃上这顿好的,我可不容易呢。”
路征那日叮嘱她,守卫不在,诸事收敛。
天地良心,今夜不肯收敛的人,是他自己。
阿亡吃饱喝足,跳上她小榻,将身体卷成一团,打起了呼噜。她也闭目,试图入眠。她还在想□□他二人亲热的那抹身影。不知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来者不善,目的不纯。
终于困倦,他的气息又萦绕她身边。唇瓣微热,好似身处云端,飘摇烂漫。恶意也可消散无形,日子也可过的久长。
可不许贪睡,明天还要早起,迎一位重要的客。
次日,娇梨院有稀客来访。自“金龟婿”佳话远扬之后,光顾瑶姬这曳烟阁的人已极少。路丞相瞧上的女人,旁人匪敢侧目。但总有那么一名年轻气盛、藐视天高地厚的,定要撞回南墙,逞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