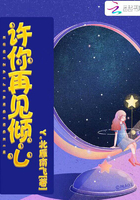战后的夏天,我们去了瑞士,因为这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战争蹂躏的国家。在6年的轰炸、配给、节俭和压抑后,我们渴望正常的生活。我们一穿过国界,就发现环境有了明显的转变。瑞士海关军官的制服很新很华丽,不像法国边境那些人的破烂制服。火车看起来干净且明亮,以新的效率和速度前行。到了卢塞恩,我们坐上以前用马拉而现在用电驱动的古典四轮车。这种车车身高大,带有厚而大的玻璃窗,正是我们的父母在儿童时期见过却从没坐过的老式车,这种老式车带着我们去了瑞士宾馆,比我想象中要宽大华丽得多的宾馆。我的父母通常会选择相对适度的住处,但是这次他们的本能带他们到了卢塞恩最豪华、最奢侈的宾馆--他们感到这是6年战争之后破例的一次奢侈。
瑞士叫我难忘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这里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开音乐会的地方。在我的钢琴老师斯利威女士去世后一年内我都没碰钢琴,但是现在,阳光和自由带我走出阴霾,突然之间,我想再次演奏,也想为别人演奏。尽管我是伴随巴赫和斯卡拉蒂长大的,在斯利威女士的影响下,我逐渐喜欢上浪漫乐派,尤其是舒曼和轻快非凡的肖邦的玛祖卡舞曲。这些曲子很多我都不擅长,但是我熟记它们,不自谦地说,我至少能弹出这些曲子的感觉和活力。这些曲子并不庞杂,却包含了整个世界。
不知我父母是怎么说服宾馆人员在它的沙龙安排了一场音乐会的,我可以使用他们豪华的钢琴(它比我见到过的钢琴都要大,是一架贝森朵夫钢琴,比我们的贝奇施坦因额外多了许多的键)。他们通告说,在即将到来的周四晚上,将有一场英国年轻钢琴师奥利弗·萨克斯的独奏会。这让我很恐惧,而且这天临近,我就变得越发紧张。但是,当那晚真的到来时,我穿上我最好的衣服(它是前一个月父母为我的成人礼制作的),我走进沙龙,鞠躬,微笑(其实当时害怕得差点失禁),坐在钢琴边上。在第一曲玛祖卡舞开始一小节时,我一气呵成,然后华丽结尾。接下来,有掌声、微笑,还有对我错误的原谅,然后我充满感情地开始了第二首曲子,一曲接一曲,最终以一曲圆舞曲落幕(我约略记得这是肖邦死后才出版的作品)。
这场演出让我感到很愉悦。我的化学、矿物学和自然科学都是我自己的,除了跟舅舅们分享外,别无他人可共享。相反,独奏会是公开的、开放的,有欣赏、互动,有付出,也有收获。它是一种新的体验,我开始与人交流。
我们尽情享受瑞士的奢华,在巨大的大理石浴缸中流连,在奢华的饭店吃到差点胀死。但是最终我们厌倦了这种过分的放纵,开始在这座古城弯曲的街道上徘徊,欣赏着风光。我们乘索道车到了瑞奇山的顶峰。我第一次上索道,第一次爬山。随后,我们去了罗莎的阿尔卑斯村,那里空气凉爽干燥,而且我第一次看见火绒草和龙胆根,还有彩绘木头盖的小教堂,我还听到笛声在山谷中回荡。我认为,罗莎比卢塞恩让我更愉悦、更自由、更放松,让我感受到生活的甜美和未来的希望。那时我13岁,13岁,多好的年华!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在苏黎世(亚伯舅舅曾经告诉我,它是大数学家欧拉的出生地)停留。其他地方都让我觉得很寻常,这个城市却因为一个很特殊的原因一直留在我记忆里。无论到哪儿,我的父亲总要去游泳池。他在此发现一个大的公共游泳池,便立即朝它飞奔去,挥舞有力的臂膀游水,就像这里的主人。但是我却性情懒惰,找到一块浮板躺在上面,想让它把我浮起来,仅仅是漂浮。漂浮时,我忘记了一切,只是躺在浮板上或是轻轻地用手划水。奇怪的放松和愉悦感向我袭来,那是一种在梦中才有的感觉。我曾经用浮板、橡胶圈或臂圈在水上漂浮,但这次,奇迹发生了,狂喜的感觉慢涨,巨大的愉悦感让我越浮越高,像是一直会持续下去,最终我在快乐中下沉。这是我有过的最美好、最平静的感觉。
我在脱下泳裤时才发现,刚才射精了。它并没有让我联想到“性”,我不觉得焦虑,也无负罪感。我只把这种感觉放到心里,感觉它很神秘、私密,一种自然袭来的幸福,让我感觉像是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1946年1月,我从汉普斯特得的私立学校霍尔小学转到了规模大得多的汉默史密斯的圣保罗小学。在这里的沃克图书馆,我第一次遇到了乔纳森·米勒:当一个黑影落到书上的时候,我正躲在角落里,读一本19世纪关于静电学里“电蛋”的书。我抬起头,看见一个异常高大、瘦长的男孩,长着一张运动型的阳光的脸,一双顽皮的眼睛,还有一头浅红色的茂密的头发。我们开始聊天,就像多年的亲密朋友。
这次见面之前,我只有过一个真正的朋友,就是埃里克·科恩,他几乎是我一出生就认识的朋友。一年后,埃里克从霍尔跟随我到圣保罗,现在,他和乔纳森还有我成了死党,不仅因为个人关系,还有家庭关系(30年前,我们的父亲都是医科学生,我们的家庭一直关系紧密)。乔纳森和埃里克不像我那样热爱化学--尽管他们加入了钠投掷实验还有其他实验--相反他们热衷于生物学,不可避免地,有时候我们会在生物课上相遇,我们都喜欢我们的生物学老师希德·帕斯克。
帕斯克是个优秀的老师,虽然他保守偏见、固执、说话结结巴巴(我们不断地模仿他的口吃),但他绝顶聪明。帕斯克先生会用劝阻、讽刺、嘲笑或是催促的方式让我们远离其他--运动和性,宗教和家庭以及我们在学校的其他科目。他要求我们像他一样,把心思全放在生物学上。
他的大部分学生认为他就像一个不可思议的苛刻的工头。他们会尽他们所能逃离这个学究式人物的专政。在挣扎中,突然不再需要做任何抵抗--他们自由了,帕斯克不再挑剔,不再针对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提出可笑的要求。
但每年,我们当中仍有很多人在接受帕斯克的挑战。与此对应,他在生物课上把一切奉献给了我们。我们晚上在自然史博物馆跟他待到很晚(我曾经想把自己藏在走廊里并设法在那里过夜)。我们要牺牲每个周末用于植物采集,我们要在寒冷的冬天于拂晓就起床,就为上他一月份的淡水生物研究课程。曾经有一年--那是我们很难忘记的甜蜜回忆--我们跟他一起去密尔堡待了三周以学习海洋生物学。
密尔堡位于英格兰西部海岸线,配备有漂亮的海洋生物观测站。在那里,我们总能受到友好的欢迎,然后被引导到他们正在进行的实验。那时,我们观察海胆的生长情况。罗斯契德对挤在他身边,盯着他那装着透明幼虫的培养皿的男学生一直都很有耐心。乔纳森、埃里克和我把岩岸分成几个横切面,数着所有的动物和海藻,自青苔覆盖的岩石顶部到下面的海岸线和潮汐积水处。埃里克尤其聪明,我们有一次需要铅垂线但是不知道怎么悬挂的时候,他从岩石下找到一个海螺,把铅垂线的一头挂在它下面,然后就把海螺像一个普通图钉一样紧紧固定在顶部。
我们喜欢不同的动物学组织:埃里克喜欢海参;乔纳森喜欢闪光的带刺的蠕虫,喜欢多毛动物;我喜欢鱿鱼和墨鱼、章鱼,头足类动物,这些动物在我眼里是最聪明最漂亮的无脊椎动物。一天,我们去了海边,肯特郡的海斯,乔纳森的父母在那里买了避暑的房子。我们坐一艘商用拖船钓了一天的鱼。渔夫们通常都会把网里的墨鱼扔回去(在英国,人们通常不爱吃墨鱼),但是我狂热地要求他们留给我,当我们回码头时,甲板上已经有很多墨鱼了。我们用桶和浴盆把所有的墨鱼都带回住的地方,把它们放在地下室的大水缸里,然后加上一点酒保存。乔纳森的父母不在,所以我们毫无顾忌。我们可以把所有墨鱼带回学校,带到帕斯克面前。我们想象当我们把墨鱼带进去时他惊讶的微笑,而且班上每个学生都将有一条墨鱼用来解剖,要给热爱头足类动物的学生两到三条墨鱼。我会在俱乐部跟他们交谈,谈墨鱼的聪明,它的大脑,它视网膜突出的眼睛,还有它们迅速变色的本领。
几天以后,乔纳森的父母要回来的那天,我们听到来自地下室的沉重的撞击声,我们下去,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墨鱼没有保存好,已经腐烂发酵,产生的气体使水缸爆破,墙上和地板上有大块的墨鱼,还有墨鱼的碎片飞到天花板上。腐烂墨鱼的强烈气味地难闻得难以想象。我们尽全力擦去墙上的墨鱼,并弄走各处的墨鱼块。我们用水冲地下室,几乎要窒息了,但是却除不掉恶臭的气味,我们打开门窗想放放地下室的气味,它的毒气蔓延至四面八方。
埃里克总是很聪明,他建议我们用更浓的好闻的气味来遮盖臭味。我们想到椰精,那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了。我们集中我们所有的钱,买了一大瓶,加水冲洗地下室及其他弄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