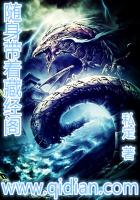战后的一个夏天,我们在伯恩茅斯海边度假,我设法从一个渔夫手里弄到一条巨大的章鱼,把它放在我们旅馆的浴缸里,并在里面放满海水。我喂它活螃蟹,它会用它那角状的嘴把螃蟹撕开,我想我逐渐喜欢上它了。当我进到浴室里时,它的确认出了我,于是变换不同的颜色来表达它的感情。尽管家里养过猫和狗,但我从没有过一只自己的动物。现在我有了,我把我的章鱼看做跟所有我想带回伦敦的狗一样聪明,一样是我的挚爱,我想给它一个家,一个极大的装饰了海葵和海草的水槽,把它当做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宠物。
我读了很多关于水族养殖和人造海水的书,但是,我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有一天,当女仆进到浴室里,看见浴缸里的章鱼时,她发疯似的用一把长扫帚戳它。被惹恼的章鱼喷出一大团黑墨水。我晚些时候回到家,发现章鱼已经死了,四肢摊开,躺在它喷出的墨水里。回伦敦后,我伤心地把它切开,想了解一些东西,并把它分解的遗体保存在福尔马林里,并在我的卧室里放了很多年。
生于一个医学世家,听着我的父母和哥哥们谈论关于病人和医学条件的话题,这让我着迷,有时也让我很震惊,但是,我的新化学词汇让我可以与他们争论。他们可能会谈论肋膜腔积脓症(empyema,一个美丽的脆生生的四音节词,却用于描述胸腔内恶心的化脓),但是我会想到焦臭(empyreuma),用于描述燃烧有机物气味的词汇。我并不是只喜欢这些单词的发音,还喜欢它们的词源。我在学校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整理化学术语的起源和出处,有时也整理它们是如何历经波折获得现有词的词义的。
但是我父母喜欢讲医学故事--通常会从描述一个病例或手术开始,延伸出整个故事。尤其是我母亲,她通常会给她的学生、同事、客人,甚至周围的任何人讲这样的故事。对于她来讲,医学总是深入人们生活的。我有时会看见送奶工人或是园丁呆呆地听着她的临床故事。
在手术室有一个装满医学书的大书柜,我会随意翻翻那些书,总是有一种又喜欢又惊恐的复杂心情。一些书我读了很多遍:约翰·布兰德·萨顿的《良性与恶性肿瘤》。这本书因其独特的关于怪异的畸胎瘤和肿瘤的素描而著称:腹部连在一起的连体婴;脸部连在一起的连体婴;两个头的牛;耳朵旁边有一颗小头的婴儿(那个头就像一个微小的复制品,只是缩小很多);“毛粪石”--吞食了大量的毛发或其他食物残渣,阻塞在肠胃道,有时会使人致命;大到需要用手推车装载的卵巢囊肿。当然,父亲也曾告诉过我关于“象人”约翰·迈瑞克的故事(约翰住过伦敦医院,而父亲曾在那里实习)。展示所有皮肤病的《皮肤病图谱》也十分恐怖。但是我读得最多的、信息最全的,是法兰奇所写的《鉴别诊断》--它小小的素描尤其吸引我。恐怖的远不止这些,最让我感到恐惧的是早衰,一种急性病,可以让一个10岁儿童在几个月内迅速变老,成为一个骨头脆弱、秃头、鼻子尖尖的人,像满脸皱纹、尖嘴猴腮的巫婆--如《所罗门王的宝藏》里300岁的老巫婆加古尔,或是拉格奈格岛上发狂的斯特勒尔布勒人。
我回到伦敦,跟着我舅舅开始了“学徒生涯”(有时我会这样想),对巴拉德菲尔德的恐惧像梦般消失了,但仍留下迷信,还有一种预感,好像那噩梦随时都会再次降临到我身上。
我知道化学实验有危险,但我愿意与这些恐惧周旋,我说服自己,只有小心、警惕、审慎、深谋远虑,才能学会控制,或是找到一条穿过这危险世界的路径。可能确实因为小心(和运气),我算是保全了自己,还控制得不错。但是对于生命和健康,我不知道有什么防护可以让人长命百岁、百病不侵。各种各样的焦虑和恐惧侵袭了我:我变得害怕马(送奶工用它来拉他的平板车),害怕它们咬我;害怕过马路,尤其是在我们的狗格里塔被摩托车轧死以后;害怕其他孩子会嘲笑我;害怕踩在铺路石间的裂缝上;最重要的是我还害怕疾病,害怕死亡。
我父母的医学书助长了我的这些恐惧,让我有了忧郁症的征兆。在我12岁的时候,我得了一种神秘的、几乎威胁到生命的皮肤病。我的手肘和膝盖流出一种分泌物,弄脏我的衣服,因此我总是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生怕别人看见。我害怕地想:难道我注定要得我曾经在书上见过的那些怪病吗?
我喜欢放在餐厅的那张巨大的铁桌子,想象如果我们遭到轰炸,它坚固到足以承受整个屋子的重量。有很多关于桌子救人的说法,那些人借桌子免于被压碎或窒息而死。当空袭来临时,一家人就会躲在桌子底下。这种保护让它像一个避难所,并且几乎有了人性。桌子能够保护我们、照顾我们、关心我们。
我感觉它非常舒适,几乎就像屋内的一个小别墅,当我10岁从圣劳伦斯学院回家,即使是没有空袭的时候,我有时也会爬到桌子底下,静静地坐或躺一会儿。
父母也发现我那时非常脆弱,当我在桌子底下躲着时,他们也不会有意见。但是一天晚上,当我从下面出来,他们看到我头皮上光秃秃的一圈,害怕极了--癣是他们立即就能诊断出来的。我的母亲近前来看了看我,然后跟我父亲小声嘟囔。他们从没听说癣会这么突然出现。我一声不响,装做很无辜的样子,把剃刀藏了起来,是我偷偷带在身上的马库斯剃刀。第二天,他们带我去看皮肤专家姆安德医生。姆安德医生看了我一眼--毫无疑问,他看穿了我的把戏--从我秃头的地方拔了一根头发样本,把它放在显微镜下检查。一秒后,他说,是“人工皮炎”,意思是头发脱落是自己造成的。听他这样说,我脸红了。后来就没再讨论为什么我会剃头发或者为什么我会说谎。
我母亲是个非常害羞的女人,她几乎不愿意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必须去的时候,她就会躲在一处,默不出声,或是陷入沉思。但是她的性格也有另一面,当她自由自在地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她会变得豪爽、洒脱,会变成一个表演者。很多年后,当我把我的第一本书带到法贝出版公司的一个编辑那里,她说:“你知道吗,我们以前见过面?”
“我不记得了。”我很窘迫地说,“我从来都记性不好。”
“你是想不起来,”她又说,“很多年以前,我曾是你母亲的学生。那天她正在做关于哺乳的演讲,几分钟后,她突然停了,说,‘哺乳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她弯下腰,抱出一个藏在她桌子底下的熟睡的小孩,打开包裹小孩的被子,当着全班人给他喂奶。那是1933年9月,你就是那个婴儿。”
我遗传了我母亲的害羞、对社交的恐惧,还有她在观众面前的挥洒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