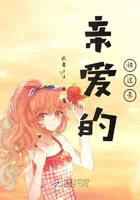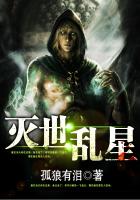在美国做董事,曾经是个包赚不赔的美差--一年挣十万美元,开六到八次会,这几次会还经常是在全球各地的风景名胜举行。有些人甚至就专门以做公司的董事为全职,我听说过最厉害的有一人身兼十多家公司的董事!但是现在可没那么便宜了,董事在继续享受各种福利的同时也要承担起更多的义务,甚至可能面临自掏腰包为自己的行为埋单的风险。
我的一个曾担任多家公司董事的朋友近来跟我感叹:“做董事真是越来越不容易了。”尤其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董事的义务越来越重。一旦股东提起诉讼,董事不仅会面临巨额的赔偿,还有可能陷入牢狱之灾。公司董事,一个曾经让人羡慕不已的美差,现在却让大家唯恐避之不及。
确实,公司治理是一个让公司股东和学者都很头疼的问题。公司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造成了现在公司治理中代理成本过高的现象。美国采用了独立董事制度,希望能够以此在股东和董事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起到保护股东利益的作用;德国则认为监视会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更好地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中国则将这两者结合到了一起。各国所采用的制度虽然不同,但目的都是一个:降低代理成本。换句话说,就是要董事从股东的利益出发为股东服务。可惜,以上这些方法都没能达到设计者所期望的最佳效果。
美国公司董事的义务
与中国公司不同,美国公司只设董事会,不设监事会。美国公司的董事会对公司的业务和事务拥有至高的权力,包括对高管人员的任命、对公司重大事件的决策,重大事件就包括决定与其他公司合并、收购目标公司、或者出售自己的公司。在拥有这些权力的同时,董事们也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其中最主要的是信托义务【Fiduciary Duties】,包括注意义务【Duty of Care】和忠诚义务【Duty of Loyalty】。无论是美国公司还是中国公司的董事【和高管】义务,其目的都是最大化股东的利益,同时降低现代经济学所称的代理成本。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董事会还负有其他一些特殊的义务,本章后面的内容将通过案例来详细介绍。
注意义务
这种义务的概念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这也是由疏忽造成的侵权行为的依据。我们知道,律师对他的客户负有注意义务,医生对他的病人负有注意义务,司机等等社会上的其他人员都对那些可能因为他们的不当行为而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失的人负有注意义务。这个概念的精神是,当一个人所从事的行为有对其他人造成伤害的危险时,一般来讲,这个人有义务谨慎行事以避免这种伤害的发生。
在公司法的领域中,注意义务指的是,董事会在进行决策时,应该基于诚信和合理注意,在充分收集信息、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公司利益为最高的前提下,做出决定。
忠诚义务
当我们说董事或者管理人员违反了他们的忠诚义务,我们是指他们过于贪婪,将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置于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之上了。在好些情况下都可能发生这种行为。最明显的一种情况就是,公司的董事或管理人员让公司与他们自己的公司签订合作的合同。另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公司的董事或管理人员发现了一个对自己的公司有利的商业机会,而抢占了这个机会为己所用。这两种情况以及类似的其他情况都属于违反忠诚义务。
中国公司董事的义务
在中国,公司法规定了董事的忠诚义务和勤勉义务,并对忠诚义务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规定,而对勤勉义务未做明确的规定。此勤勉义务应该被认为与美国公司法中的注意义务相类似。中国因为受到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影响,公司除了董事会外,还设置了监事会。监事会的作用与美国公司的独立董事比较类似,但不完全相同。这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美国三大证券交易市场对独立董事做了明确的规定,其中一项就规定了公司内部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而中国的监事会却是由股东代表和公司的职工代表组成的。中国的监事会只能列席董事会议,而美国的独立董事则完全是董事会的成员,享有董事会成员的所有权力。与董事会相比,中国公司的监事会的职权是非常有限的。在美国,监事会的这些职权是由股东来行使的。美国公司的股东有派生诉讼或称股东诉讼的权力,中国公司法的修改引进了美国派生诉讼的概念,赋予了股东行使派生诉讼的权力,那么设置监事会也就多此一举了。所谓派生诉讼是指,股东可以以公司的名义对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要求其予以纠正,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制度使得股东可以对董事和高管人员进行监督。另外,按照中国公司法的规定,监事会的组成人员不仅包括股东,还包括公司职工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这就意味着监事会所代表的利益并不只是股东的利益,还涉及相关利益人的利益,即职工代表作为相关利益人来参与公司的治理。在大多数情况下,董事会所代表的股东利益与监事会所代表的相关利益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有些时候,比如公司在进行合并和收购的时候,双方利益就有可能发生冲突。那么,究竟谁的利益应该是最高利益呢?我们在第二章的讨论已经得出答案了。另外,监事会的一个重要职权就是有权检查公司财务。如果说设立监事会的目的是想给股东一个说话的权利,那么这一点可以通过派生诉讼来解决。如果它的设立是为了给公司职工一个说话的权利的话,那么这个机制就纯属多余。因为职工与公司的关系是雇佣关系,职工的权力已经有劳动法来加以保护了,没有必要再通过监事会来保护。
一个公司的董事会如果违反了其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轻者令其纠正行为,重者则负有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是不是所有的董事会或高管层的决定都有可能违反其注意义务或忠诚义务呢?比如一家公司准备收购另一家公司,收购前收购方认为这一合并将为自己的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事实上在合并后,公司的经济效益遭到重创,这种情况下,董事会或高管层是否对他们所做的决定负有法律责任呢?如果想要控制一家美国公司,就必须了解一个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法宝”,它就是“商业判断法则”。
商业判断法则
商业判断法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0多年前。这个法则背后的原则是,当那些做出商业判断的董事们的决定产生了极差的效果,或者他们的决定是极不理智的时候,法院应该出面予以干涉和限制。这倒是不无道理的。但毕竟,商业决定都会涉及风险。结果是,也许许多当时看起来十分明智的商业决定到最后都一无所获。并且,董事们经常要面对的情况是,他们必须做出决定,但无论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会有人不满意。因此,当董事会或高管层在做出商业决定的时候,是以诚信为原则,有充分的信息,并且所做的决定是为公司的最佳利益考虑,这时他们所做的决定就能受到商业判断法则的保护,即使他们的决定后来为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也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在中国,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类似的法则,但是在经济运作中,这个法则的精神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对于那些想收购美国公司的中国企业来说,仅仅了解董事的信托义务的概念、原理和法律条文是不够的,因为美国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它是一个适用普通法的国家。所谓普通法,就是判例法,也就是说,在这种国家,一个公司不仅要遵守国家已经颁布的法律条文,还要遵守法院有关公司法案件的判例。这些判例已经成为了法律。美国公司法最为复杂的特拉华州,其公司法的收购法主要就是由判例组成的。而根据这些判例所做出的判决会随着不同的案件的具体情节而有所不同。所以如果只了解公司法中有关收购的法律条文的话,真可谓只看到了冰山一角。另外,美国的司法体系与中国的有着根本的不同。美国有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两个体系。公司法方面全部是州立法,而没有一个联邦的统一法律。虽然,2002年由美国国会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对公司治理方面做出了一些规定,但是此法并没有在收购、合并、兼并等领域做出规定。所以通常所说的收购法其实是指,美国各州公司法中有关收购和合并兼并的法律条款以及判例。所以,美国其实没有一部专门的“收购法”。如果中国公司想要收购美国公司,就需要认真了解目标公司所注册的州的收购法。另外,如果目标公司是美国的上市公司,那么收购者还需要了解美国的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所在的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谈到美国的判例法,其复杂程度在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够与之相比。在美国各州当中,在公司法立法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特拉华州,它有比较成熟的公司法原则和判例,是美国各州制定收购法的典范。特拉华州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美国的上市公司当中将近一半是在这个州注册成立的,因此这个州的判例非常有影响力。近十年来发生的公司之间的收购、反收购的战争几乎都是在这个州,因此特拉华州的公司法判例中留下了许多有名的经典案例。
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个真实的判例吧,看看董事的信托义务在现实的并购交易中是如何体现的,也看看美国法院是如何通过判决来为传统的董事信托义务赋予新的内涵和意义。在下面的这个判例中,法院第一次判决公司的董事因做出了草率的决定而需要向股东支付赔偿。一般来讲,董事所作的商业决定是会受到商业判断法则的保护的,但本案中卖方股东却认为自己公司的董事会在出售公司时,没有搜集和研究足够的信息,做出了草率的决定,不能适用商业判断法则。他们将自己的董事会告上了法庭。虽然“草率”是很难被量化来当做评判一个决定好坏的标准的,但是仍然可以通过搜集各种细节事实来加以证明。法院的判决正是依据了这些细节事实判决了卖方公司董事会的确做出了“草率的决定”,董事会成员要为自己做出的决定买单。这个案例极大地震动了投资银行界、律师界和司法界,更不必说那些向来不认为董事要为自己的决定掏腰包的公司高管层了。
也是在这个轰动一时的案例之后,要求投资银行提供公平性意见书成为了并购交易中通用的惯例。公司董事会将这个意见书作为自己的保护伞,以免再被指责为没有参考专家意见。
为什么要卖公司?
联合运输公司是芝加哥著名的上市公司,主要经营火车车厢租赁业务。在本案的收购中,并没有收购者主动提出购买联合运输公司。而是联合运输公司主动出击,为自己寻找买家。因为该公司拥有充裕的现金流,但是因为可以享受折旧减税和投资税的抵免【Investment Tax Credits】,几乎没有可征税的收入。这就使得该公司当时不断增加的投资税抵免【ITCs】派不上用场。1980年6月,该公司管理层提交给董事会的五年发展计划修订本当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年的8月27日以及9月5日,该公司已近退休的CEO范·戈康两次召集高管层讨论此事。会上,公司CFO罗马斯按要求给出了该公司通过一笔杠杆收购【LBO】出售可能达到的价格,他认为以50美元一股售出是比较容易的,而60美元一股的价格就比较困难。范·戈康不赞同公司内部高管层收购,因为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但是他表示愿意以每股55美元的价格出售。当时,联合运输公司的股票价格为每股38美元。在1975年到1979年的五年间,该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在每股24.25美元到39.5美元之间。这两次会议以后,范·戈康就让公司的财务主管为每股55美元的杠杆收购的可行性做财务方面的估算和准备。
9月13日,戈康会见了他的朋友、芝加哥有名的金融家杰·普里斯克,并向他提议将联合运输公司以每股55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他。说起普里斯克,此人在芝加哥商业界是首屈一指的几个重量级人物之一。著名的凯悦饭店【Hyatt Hotels】便是其家族生意之一。在世界家族财富的排名中,他们也是榜上有名。普里斯克兄弟是这个庞大家族企业的掌舵人:哥哥负责到处物色和收购公司,弟弟则负责经营这些公司资产,配合十分默契。
两天以后,普里斯克答复戈康说他有意以每股55美元的价格收购联合运输公司。到9月18日,经过两次有两名联合运输公司管理人员和一名外部顾问参加的会议以后,戈康了解到普里斯克的计划是如果他能以每股38美元的价格买入一百万股联合运输公司已发行并回购的股票【treasury stock】,他就愿意以每股55美元的价格与联合运输公司进行现金合并。并且他希望该公司的董事能在3天内,即9月21日之前,对此计划进行表决。普里斯克同时通知他的律师开始起草合并的相关文件。
9月19日,戈康没有咨询公司内部的法律部门,就直接与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合同为他提供合并的法律服务。他随后在次日即9月20日召集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开会。但只有那些参加过与普里斯克谈判的管理人员预先知道这次会议的目的。
两个小时决定一切
这次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而联合运输公司常年的投资银行代理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并没有被邀请参加。因为合并协议送来太晚,来不及仔细讨论,所以这份协议并没有呈送董事会,董事们也没有在会前或会中阅读。戈康只是口头解释了这份协议的内容,花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向与会人员转达了普里斯克同意给董事会90天的时间来考虑更好的合并提议,条件是该董事会不可以公开招标或者向其他有合并意向的公司提供未公开的信息。董事会讨论了一下这份协议和条件,决定接受这个协议,条件有二:【1】联合运输公司保留在此后的90天内接受其他更好的合并协议的权利;【2】联合运输公司可以向其他潜在的合并者提供未公开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