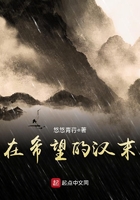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路上的行人们都在行色匆匆的往各自家中赶,没有人会注意到身着一身粗布妆扮的我们。
尽管如此,我仍将自己的帽檐拉得低低的,拉下些头发盖住了前额,再低垂着头,缓缓的走在泉州的街头上,生怕遇到赵存义的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尽管时间也只过过去两三个月,泉州此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着泉州如今四处大兴土林的模样,我内心有一团怒火在熊熊的怒火在燃烧,似曾相见的场景更是让我愤恨不己。
我身为皇上,如今也只是借居在蒲寿庚的旧宅,包括全体文武大臣此刻也是无瑕给自己开旧个安乐的窝。这赵守义的排场倒是如此之大,我才刚“死”不过两三个月,他就在这里大兴土木了。不但给自己建了占地宽广的忠王府,手下的一众从众们都是不少,那排场几乎占了小半个泉州城了,我一边走着,一边忍不住低骂几声。
凌旭和杜娟一左一右,谨慎的跟在我的身后,双眼不时警视的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一点都不敢松懈。
尽管根本不曾人注意到我们,但我们仍是学着其它行人的样子,内心紧张的进了城。又急步的穿过了几条巷子,正要挨着墙边,闪进一处小巷,却见前面的大街上浩浩荡荡的拥来一群激愤的行人。走在最前面的人手里扶着一幅足有七八尺长的横幅,上面居然端端正正的书写着“请复祖制,还我大宋”的大字。他们的嘴中不时声嘶力竭的高呼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活捉范伟松,再杀方志远。”“范伟松,妖孽,方志远,妖孽。”他们的呼声不一会儿便吸引了不少的人前来观看,可一听到他们叫的内容之后,更多的百姓只是摇了摇头便闪进了门后。生在乱世中,对于小民来说,明哲保身确实是他们不得己的选择。
杜娟一头雾水的望着这群群情激昂的游行队伍,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凌旭则将拳头捏得咯咯直响,却又生怕惊动了那些人,只得加紧了步伐,闪进了院子中,口在仍在急促的喘着粗气。
而我却留在后面,又回望了这群人一眼。他们当中,除了一些前朝官员外,还有不少象是落魄的学子儒生。更有甚者,其中还有我们这些年抓起来教育过的混混流氓们,没有想到,这一会他们摇身一变,居然成了赵守义的得力干将了。
望着这群不断的上窜下跳,嗷嗷直叫的混混流氓们和那些酸丁大儒们混在一起,我的心中早已没有了愤怒。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是一副多少熟悉的场面,曾经我的爷爷,那个只知道钻研技术的老人家,就是了几本貌似离经叛道的孤本,便被以“反革命,反人民”给揪出来了批斗。结果,本就患有糖尿病的爷爷没有挺住多久,在忧愤交加之中,死在了雨后的一个牛棚中。
父亲每提及此处,就会变得尤为悲戚。他永远都无法忘记爷爷临死前和他说过的话:“如今这个世道变得如何疯狂,但总有拨开云雾见天开的一天。你们作人,要记得要始终守住自己的良知的底限一内心的清明。做人要做得堂堂正正,这样就算死了,也死得坦然。窃不可为了一己之么便出卖了自己的良心。”
父亲将这句话刻在了自己心,也忠实的如此做了。但因为爷爷的这段经历,还在念高中的父亲便被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应急,给扔到了最为偏远的乡下。多亏了那片山村中那些淳朴善眼的人们,还好他们当中没有挂着贫下中农的名头的地痞流氓。得以让父亲在乱世中安静的读了许多的书,终于在恢复了高考之后,近三十岁的父亲如愿的考上了大学,并因为自己的专业知识留校做了教师。
父亲虽然不善经营,吃亏不少,但至少在临近退休前,仍有不少上门来真诚探访的学生。而那些保送入学的子弟兵们,除了会唱几句口号,贴几张大标语外,便只能读读几封上面的文件,装模作样的做着他们的政治工作。结果还没等到退休年龄便被内退了。退休工资又被儿子媳给了出去,听说,后来竟活活饿死在了一个垃圾堆上。
我不信命,听了这个消息之后,还是不由得感叹,这个世界上总会有报应的,天理昭彰,屡报不爽。如今不报,只是时候未到。
“皇上,到了地头了。”略一错神,我们竟又随着凌旭穿过这个院子转入了另外了个小院中。,如今望望四周,这该是处在这处待改建的破院落群的最中心了,四处都是破烂的要拆迁的房子,想必不会有人会注意到我们这里吧。
院子后面象是一条小河,还好这处房子未能让赵守义的人知道,如今我们也算有个落脚之处。
进了院子,凌旭随手将房掩上了,我们急急的穿远院子,进了左厢房中,只见偌大的厢房中,如今黑丫丫的挤了一屋子的人。
一看到我,都不由震惊了一下,回过神来,马上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围着我低声叫道:“皇上,你来了。”言语之间,竟有些呜咽之声。杜娟看到这些人见到我居然都不下跪,不免错愣了一下,让我伸手一拉,才回过神来,尾随我进了人群中间。此时,大家都有千言万语,却无从开口,只是静静的等待着我开口说话。
“今天都到了多少人。”我低声询问道。
“除了正在执行任务的兄弟,其它靠得住的人我都叫过来了。大多是我们近卫军的兄弟,以及护****中的骨干。”凌旭连忙应声道。赵守义肯定想染指我们这支队伍,但他看着这支队伍人马少,又没有真正的见识过他们的战斗力,如今也还没有腾出手来对付他们。““你们都查清楚了没有,跟在赵守义的身边的有多少人?”
“文武大臣总共也有近七八十人,也有十几户豪门大户。其它的就是一些混混地痞们级成的队伍,约有近万人。护****仍控制在我们自己人的手上,只是他们如今顶着个幼主的名义,不好当面对抗。但只要皇上一站出来,他们肯定是会支持我们的。”
“匡民那里如何了?”我又急急的问道。
“回皇上,除了小玉和张公公外,我们另有可靠的人士贴身保护,谅那赵守义也不敢如何。”
“行动之初,首先要把他们解救出来。”倒不仅是为了父子之情。我很担心我们一旦发动,年幼的匡上会为他们的人质来要挟我们,让我们束手束脚。
“朕给这次行动命名为雷霆行动,你们可要明白它的含义?”我恶狠狠地吼道,众人皆是不解地摇了摇头。
“雷霆一起,不可阻挡。只要咱们一发动,便是遇神杀神,遇佛杀佛。不管是谁,挡我道者,必然受死。”我一脸森然,语气也是从未有过的冰冷无比。没有去过安南的人,如今望着我这脸色,也不由生出凛然之色,不自觉的站直了身子。
“对于这群祸国殃民的狗贼们,我们不能给他们任何生机,不要给他们任何改正错误的机会。因为只要我们稍一心软,便有可能让他们某一天卷土重来。朕要让这些人的经历,清楚明白的告诉以后的世人们,只要一听到卖国贼、汉奸、陷害忠良、里通外国这些字眼,便会油然而生一股恨意。我们要让那些宵小们明白,别说他们真的做出些祸国殃民的事情,就是他们内心里想一想,也要让他们心里发寒。你们放手去做,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候,朕宁愿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一个坏人漏网。因为只要走漏一个,它的破坏力都是不可挽回的。乱世须用重典,矫枉何必过正。民族英雄让你们来当,千万杀星,万载骂名且让朕一个人来承担。”众人听了我这话,才终于明白了我的坚决,脸上都闪过一些不敢相信的神色。
以前就算是面对外族的时候,我都是尽量少生杀戮,他们都知道了我其实是个挺面慈心软的人。但如今他们要面对的是不久以前可能还在一张桌子上称兄道弟的自己人,内心的忐忑不安可想而知。
“你们还听不明白朕的话吗?难道你们一定要等他们将屠刀架到了我们的脖子上,把全中华帝国的百姓们都驱使成为奴隶之后才会醒悟吗?你们难道不知道除恶务尽的道理吗?”
“属下明白。”不少人的心里都不由生出一股凉意,但一回想起可能有的后果,还是为自己刚才生出来的妇人之仁感到内疚。
“皇上,忠王他?还有,他的身边好象也有些皇室宗教族,前朝遗老,是否也……?”又有人小心翼翼地问。
“我赵氏没有这样的宗亲,他们这样的人,不仅让我赵氏蒙羞,更让全中华百姓以他们为耻。而今,我们就要彻底的清除掉这群垃圾,用他们的鲜血和头颅,来告慰北方的徽钦二宗以及几千的皇室男女们的冤魂,告慰那临安城中,死了都不能安生,尸骨差点同猪牛畜类们的枯骨混居一处的列位先皇及其宗室们。告慰崖山之下,那些不屈的飘浮在海上,死无葬身之地的忠义军民们的冤魂。我们要以最强的声音告诉这个世界,崖山之后,我中华将会更强更盛。我们要用我们的双肩,用我们的双手,重塑一个血性的、强壮的、自豪的民族脊梁。我们要用他们的鲜血鲜明的告诉世人,中华,是所有中华人的中华,岂是赵守义、赵守业那些宵小们可以出卖得了的。”
这群年轻人,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崖山的惨烈。但是他们身边的许多老兵都是从那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所以,就算是时隔多年,每当有人谈及此事,大家仍是义愤填膺,或者泪流满面,甚至抱头痛哭。因为,那是属于我们全体国人的一份耻辱,那些悲壮的场面,我们一样的感同、身受。
我愤怒的语言便象一支火把,此时已经将屋中所有人心中的怒火点燃。屋子里,除了杜娟,皆露出了恶狠狠的几可杀人的目光。杜娟虽有些不解,但也似受了些影响,情绪也有些高涨起来。
“皇上,还有那些外国使者们呢,我们要如何办?”又有人问道。
“什么外国使节。”我疑惑道。
“都是赵守义请来的,计有元朝、吐蕃、日本、高丽等十几国的使节们,说是要共同探讨各国共推大宋国为天下共主,岁岁朝贡的事宜。“放屁,我忍不住就想暴粗话。如果国内仍在扰民不己,大半的国土也还在外人手中,时刻要提防着敌人来袭,若不是陈吊眼、随长信、唐克强等堵在了蒙元的第一线,只怕蒙古人早就打过来了。他们谈?凭什么和人家谈。
“咱大中华帝国可是礼仪之邦,可那礼仪只是针对那些诚心同我们交往的外邦而言。对于那些居心叵测,只想前来捞好处的使者,你们都应该知道怎么做,不要朕再教你们了吧。他们怎样来的,照例送他们一些大礼回去。咱是大国,可不能省了礼数是不是?”众人望着我一脸不怀好意的样子,似乎明白了一些。人群之中,还有不少人发出了坏坏的笑声。
“皇上,还有我呢,我的任务是干什么?”看着大家都三三两两出去了,杜娟也不甘寂寞的说。
“你的重大任务便是保护好你的好老公,其它的事情不要你担心,可不要让让那些发现你老公我了,使上些小动作,那咱们这一顿岂不全白忙了。”杜娟想要分辩几句,但一看守在门口那两个护卫饱含深意的笑容,不由马上变得满脸通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