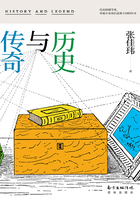第一章:(第一节)
话说这一年,红城遵义,时值盛夏,正是骄阳似火的时节,易铭这个时候过得很不如意,他在城里一家建材公司就职。这家建材公司只对外承接室内天花板的生产安装业务,公司很小,小到几近可以忽略。公司是典型的前店后厂作坊式的微型企业,算上老板在内总共就那么十来个人。成员也极端家族化,除了易铭以外,都是些亲连亲、戚连戚的角色。如此说来,单单以此而论,就没有一点现代企业的样子。
老板姓丰,四十来岁,身材不高,身体已微微发福,时时都爱笑,因眼睛小小的,笑的时候就咪成了一条缝,让人感觉特别有亲切感。他早年在广东务工,十年八年下来,就有了一点基础,积累了一些经验,于是返乡创业,创办了这家建材公司。
老板娘大家都称之为花姐,身材“魁伟”,长得过于“豪放”,五大而三粗:个儿大、嗓门大、脾气大、****大、眼睛大,以及腰粗腿粗脖子粗。做起事儿来风风火火、雷厉风行,一个人能里能外、身兼数职。公司的财务、人事、后勤、销售主管等,大事小事眉毛胡子她一把全抓。
易铭的任务就是和一个姓赵的年轻人跑销售,此人是老板表弟,刚从大学出来,外面工作不好找,就赖在他表哥这里,权当在这儿实习。他时常会飚几句英格里席,身上带有笔记本电脑,如同情人般看重,整天上网玩游戏,上厕所也形影不离,除此之外,干啥啥不会。
其他七八个亲戚平时是生产工人,围着不大的厂房忙上忙下,整天和水泥、玻璃纤维打交道,以至于服装总是被侵染得花里胡哨,手上也被玻纤扎的如同刺猬。如若业务来了,这些人就摇身一变,立即成为安装工人,马上拉出去,寻着活儿就干,效率奇高。这些人中有老板的大小舅子、表兄姐夫等,都是些前脚甩了锄头、后脚就踏进工厂大门的乡里人。
在所有员工之中,易铭是唯一通过用工市场招揽来的业务人员,工资算开得最高的了。可能就因为这样,数度让丰哥很是为难。他私下里对易铭不止一次地倒苦水,说这厂里头亲戚之间的关系处理起来尤其艰难,名义上都是他的工人,实则小心对待犹如祖宗。况且这活路都是哄着干,一个也不敢得罪,甚至就他们推诿扯皮磨洋工也不能说什么,就这样还总是嫌钱少。他们看到易铭进公司一两个月了,什么贡献都没有,开的工资却高过他们,于是全体为丰哥感到不值。他们认为:易铭每天上了班、签了到就跑出去,连人影都看不到,说易铭在外面悠闲自在、不务正业也说不准。
易铭内心知道,这是丰哥在借他人之口说自己,对此,易铭自己心里有数。至于那帮工人,自他第一天上班起就对他怀有那么点敌意,同时对他满是怀疑。在他们看来,易铭年纪轻轻、阅历不深,又好高骛远、行事漂浮,把公司建材销售这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他这么个年轻人,似乎不是太靠谱。
面对这种怀疑和敌意,易铭心里倒无所谓,因为他没有真正把这公司的业务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只是眼下呆在这里,权宜之计而已。他心里无时不刻不在挂念着的,是他与李千秋一年前的约定,他知道,李千秋神秘莫测,几番预测下来,神乎其神,只是他一再这样做,让易铭感觉其背后肯定隐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动机和目的。对于件事情,易铭左想右想,还是琢磨不透……。
其实像丰哥这样处理易铭的问题,其实还算委婉和仁义,放在有些老板那里,以易铭这种表现,或许早就结账走人了。丰哥对易铭还是抱有期望的,公开场合力挺易铭,说他第一次看见易铭,就知道易铭有从事这一行的天分,像极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他相信自己的感觉。
易铭对此也感激万分,所以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为这丰哥争口气。不久后,果然时来运转,通过易铭努力,终于促成了一桩大大的业务,公司上上下下整整为此忙活了两个来月。
看样子丰哥和花姐都很满意,忙活完了,待验收结了账,夫妇俩请公司上上下下在一家酒楼伺候,一起给易铭庆功。酒后忘乎所以之际,丰哥对易铭说这单业务做下来,公司一年的开销都不愁了,所以他翻来覆去地承诺,要兑现给易铭先前约定好了的奖金。
易铭嘴里说着感谢,但心里深知:丰哥虽然心里厚道,嘴上说着诱人,但花姐那里通不通得过才是最大的问题。
果然不出易铭所料,花姐只兑现了其中一小部分,余下的则找了个强词夺理的理由,她说要等易铭工作年限满三年后再全部兑现。因为此事,易铭与花姐大吵一场,但远不及花姐“勇猛”,以致迅速落败。丰哥则再次充当和事佬,低声下气地在易铭面前说了不少好话,又陪他喝了两次小酒,看在丰哥情份上,易铭没有再作坚持,只是后来敷衍懈怠的更甚了。
丰哥与花姐两个一唱一和,又决计不赶易铭走,目的却明显不过,他们期望易铭以后时不时或再做成一单两单同样的业务,那样的话,他们这个要死不活的企业还能够生存得下去。
但自此之后,那些工人对易铭质疑的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易铭抽烟喝酒、打牌小赌,从此不再见外。易铭知道,这圈子再小,也是江湖,自己通过这么一桩业务,算是在这儿立足了。
但易铭深知,这家建材企业生产、安装的产品很单一,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条件下,业务开展得异常艰辛,前途可谓一片渺茫,或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垮掉了都难说。他虽然明白再呆在这里,不可能有什么前途,但眼下自己境况窘迫,不容许他东想西想。鉴于已说过的原因,所以他只好得过且过,做一天算一天。至于这单业务的由来,以后会有涉及,这里暂且不表。
李易铭生于70年代,是个农村孩子,自小在农村长大,不可避免协助家里干了不少农活,也独立地种过一季庄稼,插秧犁田、挑粪砍柴,什么都算干过了。本来这也不值一提,毕竟村里那些人,面朝黄土背朝天,人家一辈子都这么干。
但易铭后来一不小心,就混进了城里,上班下班买菜做饭、三点一线,如此浑浑噩噩过了一些时间,感觉城市里的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
城里的姑娘比他老家的漂亮时髦,会穿着打扮,见识多,举止大方得体。大多生性开朗,很少矜持腼腆,只脾气怪怪,甚至矫揉造作,令易铭不能适应。虽然易铭心里幻想着努力俘获一个当做媳妇,无奈人家眼睛往天上看,易铭农村娃一个,自然战斗力有限,所以十回八回,易铭总是吃败仗,久而久之,易铭的那些想法便烟消云散了。
易铭五官也还算协调,不少人说长得帅气,个儿一米七十有五,身材更好,匀称,不胖不瘦。打小农活干的多,挑过大粪扛过木料,身上尽是腱子肉,所以有一把子力气。
一日有女同事叫帮忙扛煤气罐,易铭只手提了,一气儿中间不歇就上了七楼,大气不喘、小汗不出。那姐姐惊异不已,夸着说道:“你可真厉害!”于是极力张罗着几次三番给易铭介绍女朋友,后来见易铭除了力气,则什么都没有,所以竟心灰意冷、偃旗息鼓了。易铭如此虚度了几个年华,错过了不少好姑娘,直至后来被扫地出门。
易铭前脚被清算,后脚就去了广东,那儿什么都好,就天气热得让你疯狂,干了不足一年,易铭打起了退堂鼓,就到了丰哥这里……。
眼见六月已到,这天易铭百无聊赖,到公司报了个到,对花姐说要出去外面联系业务。花姐只用一对牛眼瞪着易铭,一个字儿也不说,易铭按照惯例,知道这算默许。
他出门后却径直回了住处,躺在床上又睡了两小时回笼觉。时值盛夏,因天儿太热,呆在床上睡得大汗淋漓,感觉租住的房子里此刻就活像蒸笼,自己像被上架蒸着的包子,浑身都熟透了。他翻身起来,又去冲了个澡,感觉好受了些,看看时间,正早上十点来钟。在屋子里东看看、西瞧瞧,无聊至极。
在这城市里,虽然老乡不少,但却没有人有空陪他。他们上班的上班,做小生意的做小生意,易铭和他们来往不多。这些老乡中,大多数还处于把生存当做生活的全部主题的紧要关头。他们总是为了将来不确定的美好日子,放弃了生活中所有的休闲娱乐。在他们眼里,看见易铭一天优哉游哉、东逛西逛,浑浑噩噩、不务正业,感觉和他们明显不是一路人。所以偌大的城市那么多的老乡,没有一个和易铭处得来,易铭也觉得自己有些另类。他自己过得不怎么样,却看不起他那些老乡,认为他们活得太苦、太累,来到世界上,只更多作为一趟艰苦的旅程。所以城市虽然大,易铭认识的人也不少,但其实根本无甚去处。
六月早上的天气已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易铭不敢想正午的骄阳,可以肆无忌惮成什么样子,一念至此,他就不自觉猛地冒了几把黏糊糊的臭汗。他不愿就这样呆在住处,但想到李千秋和他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出门眯着眼睛看了一眼天色,他就不可避免地骂了娘。因为约定的时间正是中午一点,而地点则是在不远处的公园。临走之前,他想当然以为那里有山有水,绿树成荫,要耍头有耍头,要看头有看头,必定会比住处清凉不少。
于是他出了门,随意叫了辆出租车,开车的是个长得不怎么样的中年大姐,但十分健谈,说话像旁边那家商店批发纸巾,一摞一摞直往外撂。她也不管后座的易铭有没有听,就一路的唠叨抱怨。埋怨交通,感叹人生,抱怨社会,赌咒天气,心态明显大有问题。在等红灯时,见有人开车不守规矩,于是将头探出窗外,大骂一声:“神经病!你他妈找死啊!”随后狠踩油门,一阵狂飙。
易铭见她修养不够,心生厌烦,只好扭头看车窗外,骤然看见认得的一个老乡,路边骑着一辆三轮车,沿街发他那些网点的矿泉水。易铭感叹:这么热的天儿,真找钱不要命了!
就是这个家伙,不分白天晚上,累死累活找了几个辛苦钱,未见得生活改善多少,无可阻挡地,居然连老婆也跑了,留了个七八岁的儿子给他。他也很倔强,花了不少钱让儿子读市里最好的小学,杂费超过他爷儿俩生活费。易铭劝他,他则说:“老子这样辛苦,就是自己读书少、没文化,不能让儿子再这样,自己哪怕要饭,都绝不亏欠儿子。”
易铭听了,就感觉他是在和整个世界以命相争,心里为这家伙难过得掉泪。见他生活不易,易铭也转念想想自己,觉得自己其实活得也不怎么样,就这样想着想着,不觉目的地已到。
他在公园入口的小卖部买了一瓶水,认为山上绿树荫下,可能好受一点,说不定还可以邂逅漂亮妹妹。于是他拾级而上,因一路上喝了不少的水,到了山上,感觉肚子有点不爽,不想再走,就顺势坐在路边草丛中,再也不想起来了。
阳光越发变得恶毒,山间没有一丁点的风,他举目望去,天上连一丝云也没有,这骄阳晒得他躲在树荫下也觉得燥热难当。山上山下,草丛林间,易铭发现并没有几个人,况且大多都是些老头老太太,一个漂亮妹妹的影子都看不到。
他本想躺一下,但很快意识到草丛不是棉絮,那一根根青草犹如一支支短剑向上直立着,人家正是生长旺盛期,所以躺上去感觉并不舒服。他又想睡在路旁石板上,发现已被太阳充分加热,就连用手摸上去都让人烫得受不了。他找来找去,发现没有理想的容身之地,于是只好在草地又坐下来,酷热难当之际,心中无名火气在升腾,他心里骂了李千秋何止千百回。